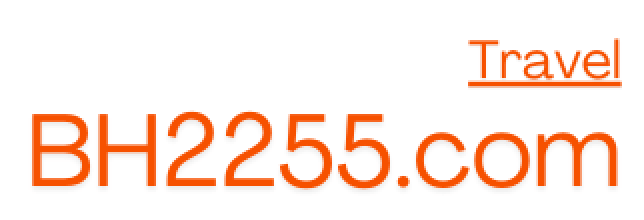敬翔游记第21篇丨《东北行》第廿一回
大青沟地理奇特,蒙族歌风采依然
在广东,昨天穿短袖今天不用说也是一整天穿短袖了。在东北,穿衣是个头痛的问题。早上7点多起来,我穿了短袖衬衣。到了9点,发觉昨天艳阳高照的天气不见了,阴天让气温下降了许多。当然,阴天不是造成降温的主因,关键是今天风大,估计有3-4级,刮风和下雨都会使东北的夏天气温急剧下降。我换上长袖还不够,再加一件外套才觉得踏实。这边的天气真的不好把握,有些年份清明节还能下大雪,而之前数天则有夏天的感觉,冬夏之间随机变换。不过,今天的街上同样有人穿短袖,这得看你的身体状况了。
今天要去的是离通辽市区将近100公里的大青沟景区。9点多才出发,同行的竟然是民族大学的海教授和几位老师。我不得不佩服王校长,她知道我这样的书呆子肯定对蒙古族文化刨根问底。
将近11点的时候,我们进入了大青沟景区,首先看到的是一片蒙古包式的餐饮店,这些蒙古包如果放在我们广东,肯定成为一个旅游点,因为我们南方人看着蒙古包就觉得新奇。旅游的目的就是增广见闻,就是要看看别人并不觉得新奇而你觉得新奇觉得东西。

这些餐饮店不同于我们广东的大排档,却又不像一家大型酒店。他们像蒙古军队安营扎寨那样分成几个大营(可能每个大营相当于一家酒店),每个大营里面整齐有序地排列着若干个蒙古包,每个蒙古包就是一个餐饮包房。通道宽阔且整洁,既看不到大排档那种污水横流、废纸巾满地的场景,也见不到空气中弥漫的油烟。不像走进酒店,倒像走进一个度假村。

这时的风很大,冷得我不自觉地把上衣的拉链拉到了脖子。这感觉,就像我们广东的初冬。也许是体质问题,也许是习惯问题,海教授和黄先生依然穿着短袖。
走进预定的蒙古包,我马上觉得暖和了许多。
里面按照牧民的摆设习惯进行布置,正中位置必定是成吉思汗的画像。一旁的炉子正在煮着奶茶,穿着蒙古服饰的服务员为我们舀起一碗碗还在冒着热气的奶茶。

我以为那些服务员仅仅只是穿着蒙古族服装而已。许多旅游景点为了突出民族特色,所有服务员都穿着当地少数民族已经不穿了民族服饰,但他们也许没有一个是这个民族的人。
海教授用蒙语和服务员交流,大概是询问与餐饮有关的问题。服务员竟然用熟练的蒙语对答如流,我这才相信她们那身衣服并非只是道具。
“我听不懂蒙语,但觉得跟日语差不多。”我记得在前往鄂温克旗的途中那位女司机说过:“蒙族人上车后就是哇哩哇啦的一通蒙语”,然而究竟蒙语像不像日语?不知道。因为两种语言我都不懂,于是向海教授请教。海教授巧妙地作了回答:“蒙族人学日语特别容易。” 是礼貌应付?还是真的有点类似?显然,我不应再问下去。(下图:坐着的女人是王校长,胖男人是海教授)

桌面上摆着蒙古人喝奶茶的食品,其中炒米是不可少的,这东西和奶茶吃下去会发胀,很长时间不觉饿。当然还有奶皮以及点心类食品,这些都是蒙族牧民早午餐的食物。虽然在商业化的餐馆里,但这回着实让我体验了牧民的饮食习惯。

几口热奶茶下去便去掉了刚才门外阴天里刮风的寒气,几把炒米渐渐地让胃里充实起来。看着时间不早,便开始进入大青沟了。
对于雨量充沛的南方丘陵地带来说,大青沟这样的景观算不上神奇,在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到处可见这样的沟壑。大青沟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处于一个奇特的地理环境:这条总面积12.5万亩的阔叶林深谷本来没什么奇特之处,它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横卧在哲里木盟南部的原野之上,与长约250多公里的科尔沁沙带相接壤。换句话来说,它的周围就是已经沙化了草原,大青沟与沟外的沙化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沟内被各种植物覆盖着,不管是乔木还是灌木,都生长旺盛,让人觉得来到了一个热带雨林,当然,你不可能看到只有在低维度才能生长的菠萝蜜、橡胶树–因为,这两种植物以阳江为界,往北则不能生存,越往南生长越好。
小时候看过连环画《嘎达梅林》,当时觉得那是在遥远的北方,那位骑着骏马挥着军刀的蒙古人的民族英雄至今仍然印在脑海里。想不到沟里竟然有一条嘎达梅林小路–传说那是嘎达梅林当年被官兵围困时的逃生小路。不过,当年并没有路,是嘎达梅林的马闯过树林带他逃生的。

大青沟内竟然可以漂流!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但仔细想一下也就不难解释了:在一个四周沙化的凹地里,并非24公里长的沟有多大的集雨面积(下雨时雨点都被沙地吸收了,流不到沟里去),而是最深处达100米的凹地汇集了周边的地下水,茂密的树林很好地调节了水的储量和流量。
这是一个水流较为平缓的沟渠,可以很轻松而又安全地进行漂流。之所以说它安全,是相对于那些弯道多、水流急、落差大的漂流区而言,在这里,你甚至可以躺在橡皮艇里打瞌睡。

王校长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漂流用具—打水仗的水枪和雨衣。但这些温和的成人玩具和那些直接拿着水瓢的年轻人来比只能算是小儿科。我在他们疯狂瓢泼的面前停住了,那些湿透了的身体上充满了青春的活力–那是我们的过去,无法再次回去的时光。不过,逝去了的青春换来的是丰富的阅历。

晚饭仍然在中午那座蒙古包里用餐,有烤羊排、牛肉干、手把羊肉和茄子等,有很多都忘记菜名了,但我发现,昨天吃过的菜式绝对不会重复,当然除了不是菜的奶茶,这个是每顿都离不开的,它就像我们酒店里的茶水一样–你不得不佩服王校长的待客之道。

喝酒是免不了的。喝的也是当地的酒,酒名就叫做青沟酒。
也许是玩得开心,这一顿喝得也痛快。我当然不会放过欣赏蒙语的机会啦:“不如请海教授用蒙语为我们表演一首歌,好不好?”
这个建议当然得到热烈响应啦,心理咨询师胡老师自告奋勇:“海教授唱蒙语,我唱汉语。”看看,他们不仅热情,而且想得很周到–怕我听不懂,来个现场翻译。
他们唱的是草原迎宾曲。
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一种认识:草原上的歌是粗狂豪迈的。理由很简单:在广阔的草原上呼唤一个人,不仅要大声,而且还要用两手做成喇叭状,还必须是顺风,否则,千米之外的人怎么能听到?可想而知,如果在草原上唱首《今夜你会不会来》肯定没人知道你在唱歌,前面那段别说离得很远,就算站在歌星的身边也听不清他唱的是什么,只有提高了八度之后才听清楚了“今夜你会不会来”这句。
《草原上的人们》几首插曲都是豪放的高音歌曲,其中的《草原晨曲》就不用说了,就算《敖包相会》这种包含着细腻情感的爱情歌曲,没有力气还真唱不了。
然而,随着蒙古族人向城里迁移的趋势,蒙古族歌曲受汉文化的影响以及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很多情感歌曲在保持了蒙歌基调的基础上让音调变得柔和了,这就使得《套马杆》红遍大江南北。
我不知道海教授的迎宾曲唱的是哪一首,但他的唱腔却是地道的蒙歌唱法,音调变得柔和了的草原歌曲却还能散发出草原的韵味。
蒙古族是能够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传承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少数民族之一,但蒙文、蒙语的传承却不如朝鲜族,大多数蒙古族人已经看不懂蒙文也不会说蒙语。尽管在内蒙古境内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以蒙汉双语标识,但基本是聋子的耳朵–用来摆设罢了。能看懂蒙文的内蒙古人并不多,像扎兰屯的白老师那样可以用蒙汉双语讲课的老师恐怕已不多见,像海教授这样专门研究蒙语的学者那就更少了。
当今许多少数民族既没有自己的语言也没有自己的文字,服饰也汉化了,风俗习惯也和汉族大同小异,这样的民族实际上已经消亡了,唯一能够证明他们民族尚存的,就只剩下身份证上所写的民族类别了。
但是,一个地方的文化总有遗留的痕迹。在这些痕迹中,有些需要通过文物考古、历史记载来寻找,如鲜卑族。有些则在文明程度较低的古村落里尚未完全消失,如满族。这个随着清朝的建立而盛极一时的民族,仅仅百年时间便找不到翻译满文的人才了,是消失速度最快的民族。
蒙歌,就目前来看,不管它的风格怎样汉化都还保留着它磨灭不掉的文化痕迹。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第廿二回结局篇:马头二弦琴声远,哈达三尺友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