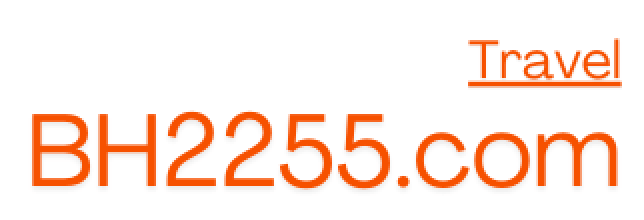在资讯发达,人人见多识广的今天,古城不再是一个具有光环、魔力、行动力的词汇,假设某人某天游了一个古城,如果不是有什么奇闻艳遇,简直都不值得写下来,看的人就更少了。很难想象,曾经“古城”也是一个热词,人们到古城去抚今忆昔,去放空,去相遇。
既然如此,喀什古城为什么会吸引我们专程前往?它是我们在新疆的第一站,每一个选择后面,总会有一些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理由,我们的理由就是没有人反对:
“下个月去哪里?”
“去喀什吧。”
“好。”
于是,就这么素履以往地定了,然后开始憧憬,期待一段好时光。



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将华夏文明、印度文明、罗马文明与埃及文明这四大人类文明汇聚一点,这个点,不在别处,就在新疆南疆。”
季先生说的是南疆,我自动代入了喀什——一个历史与文明的十字路口,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圣哲之书,同时,沙埋文明、活色生香。


我是一个古城爱好者,各种“古城”虐我千百遍,我待古城如初恋。我的古城之旅是从意大利开始的,三个全世界都知道的古城: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
威尼斯,我为它和画册一样美而陶醉,当年照片里冒着傻气的我,脸上洋溢着梦想成真的幸福。夏天的威尼斯,游人如过江之鲫,连他们,也成了我眼中的风景,我甚至学会了分辨游人们的国籍:个子高高、背着背包的是德国人,挎着相机的,是英国人,大叫大嚷、永远光着膀子的,是美国人。
一整天,我都处于幸福和兴奋当中,为“它真的是威尼斯”或者“威尼斯是真的”而感动,大运河是真的,圣马可广场是真的,鸽子是真的,教堂绵绵不绝的钟声是真的,水上的建筑和宫殿是真的。
我迷失在五光十色、眼花缭乱的景色当中,这样的兴奋一直持续到晚上。


谢天谢地,威尼斯的夜晚没有灯光工程,用“黑黢黢”来形容也不为过,我们坐在人潮褪去的船上,游览晚上的威尼斯。
当眼睛适应黑暗之后,我开始感受威尼斯的另一面,运河散发出浓郁的大海的咸味,黑沉沉的建筑在水中象岸一样沉默,威尼斯不再是耀眼的“旅行纪念品“,而是腐朽、败落的,运河的水拍打着建筑的门廊、台阶,船过处,白天的“宫殿”显得光秃、密集、暗淡、杂芜。
这也是真实的威尼斯,它曾经是一个炫富的城市,各种各样的东西,源源不断被运到这里:希腊圆柱,东方香料,波斯地毯,拜占庭杂货,锦缎,哥特式建筑和文艺复兴艺术品。这一切,到底是文化还是财富?说不清。威尼斯给人的感受是复杂的,它备受宠爱,同时又饱受诟病,有人说它乏味、肤浅、空有排场,因为只有堆砌,没有创新,它引以为豪的巴洛克建筑,当历史上真正的巴洛克式兴起时,威尼斯城又已是望尘莫及。

我以为,威尼斯的魅力正在于这种复杂的呈现,它是独一无二的,有过繁华,有过衰败,有过崛起,也有过堕落和沉沦。
无论怎样的评说,都比不上亲自去走一趟,去感受它的味道与声音,还有擦肩而过的快活的游客们。
我又想起罗马的一件小事,同样是晚上,我们在万神殿前的广场排队买冰淇淋,队伍很长,冰淇淋很有名。我们前面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四五个孩子,疲惫不堪的样子,她们给自己和孩子各买了一个蛋筒冰淇淋,孩子们吃了两口就不愿意吃了,将蛋筒塞给爸爸妈妈,开始投入更加快活的追逐打闹中,于是这对年轻的父母每个人手中3-4个冰淇淋,沉默和无奈中狂舔不已,夏天的罗马,即使晚上也很高温,他们在和冰淇淋融化速度赛跑。任何时候想起这个画面我都能笑到肚子疼。
这就是我的旅行,每一条街道,每个人,每一桩事,都有可能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只有过去很久之后,我才会知道哪些被我记住了,哪些已然淡忘。

当我打算将所见所闻写出来的时候,又觉得描述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未免有点不好意思。
对于喀什噶尔,我也会有这样的顾虑,好像我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又不想人云亦云地将城中建筑罗列一遍,实际上连我自己也没有参考过那样的一篇指南。
为了不漏掉一点罕见的美好的东西,我和同伴在方圆3.5公里的古城将脚板都快磨光了,漫无目标,随遇而安,时不时看看地上的砖,如果是六边形,就可以放心往前,总能找到通向另一条路的出口,如果是方砖,就准备回头,因为这是一条死胡同。需要注意的似乎只有这一点,其他该吃吃,该喝喝,该搭讪就搭讪,该拍照就拍照。

一些我们经过的地方:
百年老茶馆边上是一座手织毯商店,很多年代久远的老物件,旧的颜色在燃烧,比新的颜色更灼热,更迷人。


楼下突然经过一列驼队,喀什是中亚沙漠最大的绿洲城市,城里出现驼队就像草原经过马群一样正常。然而我被迷住了,仿佛碰到了走秀,不,比走秀还要优雅和好看。


如常生活的当地人:


偶尔别忘了抬头看看,特别是黄昏时的鸽群,几十只,上百只,列队飞过,洁白的翅膀反射着太阳的光芒,像是在为某一场大型演出在排练。
话说我仰头看鸟儿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也许是我的样子太奇怪,一会儿就有好几个孩子围着我,后来越围越多,大家一起仰头向天空看,她们说鸽群在满天找吃的,鸽子飞过来的时候,孩子们就会大声提醒我:来了,来了!
有了他们帮倒忙,我反而拍不到鸽群,太吵了。
不过没什么,和孩子们一起玩,不是比拍鸽子更有趣吗?他们问我去哪里,我指着路牌说我在找一个免费观景台,孩子们马上七嘴八舌通告内情:“早就没有了,我小时候就没有了。”可他们看起来,似乎都不超过七八岁。
我走的时候,孩子们舍不得:“你不能再玩一会儿吗?”就在我犹豫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转移了注意力,好吧,再见了,小可爱们。



离开古城,我一个人去了香妃墓,去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
香妃墓又叫阿帕克霍加麻扎。阿帕克霍加是17世纪中晚期伊斯兰教白山派的首领,他以喀什噶尔为基地,统治南疆六城,创建了天山以南第一个政教合一的“霍加”政权。香妃作为阿帕克霍加的重侄孙女,在这个葬有五代七十二人的显赫家族墓地占有一席之地。
二十多米高的陵墓,有着方形的底部和半球形的穹顶,四角耸立着高高的邦克楼,陵墓的外墙镶嵌绿色琉璃砖,夹杂着蓝色和黄色,通体呈现出伊斯兰建筑庄重、稳重、圣洁的特征。还有绿拱北、高低寺、门楼、水塘、果园和花圃。
香妃墓十分适合黄昏时一个人造访,绕着建筑一圈一圈地走,感受空气以及能量的流动。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增加了香妃墓的魅力,即使单单作为一处场所,一座建筑,它依然美轮美奂。




从香妃墓回酒店的路上,迎面碰上了吐曼河上的日落,河水和桥被涂上一层美丽的金色,那是喀什噶尔本来的颜色,“黄金和美玉之城”。我停下来看落日,看桥上互拍的维族少年,一代又一代,传统和现实,喀什噶尔是本真的、深邃的,神秘中珍藏着古老的个性,它也是放松的,自在的,无论外面多么焦虑,我们都能在喀什噶尔找到安宁和温柔。哪怕这不期而遇的夕阳,也不是刺眼的,而是安抚的,柔和的。


第二天我们离开喀什,经疏附、乌恰、阿克陶县前往塔县。
南疆旅途的每一天都令人陶醉,相比景色的优美和浑然,文字总是显得笨拙。
谢谢你愿意听我继续讲述路上的故事,下一站,帕米尔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