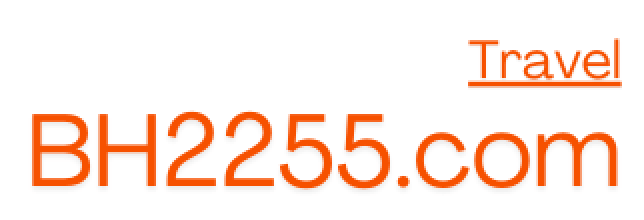2020年2月6日深夜的那个夜晚,我很难过,你“能、明白”么?
伊洛瓦底江畔的木偶让我忍不住想知道人生究竟意欲何为?
佛祖说要开启智慧,要心生慈悲才能令世人醒悟,要明白一切皆为虚空,不再堕入轮回才是真正的解脱。

我以为,人生之戏,木偶就可以演,人生的感悟,还是需要用心灵去体察。所以生的意义在于感知,无论是欢欣还是悲痛;在于思辨,以洞察是光明还是黑暗;在于选择,是苟且犬儒还是在理解虚空之后依然坚定地选择在红尘中逆行,去拯救苍生。
人生苦短,我们都不是英雄,也不想做什么英雄,我们只想明白活着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一只白喉鸫鹛飞到眼前,夕阳照在它的身上,令它像奥林匹克山上的穿着金色长裙的神祗,光芒闪耀。这是多么美的画面啊,这就是活着的价值。
活着,才能知道这个世界的美好,为了感知这样的美好,我们才要活得有尊严;为了守护这样的美好,我们拒绝同流合污。

站在蜜糖色的佛塔前,我意识到这些年自己的选择是多么幸运。
白喉鸫鹛是缅甸特有的鸟种,集小群生活,彼此之间又相互独立。无论是立在枝头还是钻在灌木丛中,它都保持着对世界的观望。

它不畏惧人类,但也不像家麻雀那样与人类过分亲昵,它是属于旷野的鸟,即便就在村落周围生活,它也是自由的,不受地上那些谷物的诱惑,而是自己在枝头寻找食物。它的眼神白多黑少,看上去有些难以亲近,然而它又是欢乐的,它不需要我们。再说一遍,它是自由的。
有不自由的鸟儿么?

原鸽因为田地里散落的食物而迟迟不肯离去,即便我已经走得很靠近。白斑黑石鵖和东亚石鵖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个是本地鸟儿,一个是千里迢迢赶来越冬的外来客,还好它们都没有排外意识,愉快地共享这片土地。还有纯色山鹪莺,一种国内华南地区再常见不过的鸟儿,在这里却因为过于大胆,竟让我不敢相认。

望远镜里出现了一只杂色松鼠,它用在佛塔上的酷跑表演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脚下忍不住就走了过去。忽然,脚边的草丛中飞出一只棕三趾鹑。看它急匆匆的样子,应该是被我惊吓到了。我也被它吓了一跳,怔在那里不动。
世界仿佛陷入了寂静。
我有些懊悔事先竟然没有发现棕三趾鹑的存在,尽管我知道以它完美的保护色,那是不可能的事。等我终于放弃念头,重新迈了一步,万万没想到又飞起一只。
这下心底真的不淡定了。可是脚下的草很深,它们究竟躲在哪里?毫无蛛丝马迹可寻。无奈的我只好继续走,它们继续从草丛里窜出,然后如烟花四散,前前后后一共六只。

我的心简直在滴血。那棕三趾鹑长相似乎有些怪异,但是它们每每毫无征兆地忽然窜起又快速的落入草丛,令我根本无法仔细观察,即便我有十五年的观鸟功力也是枉然。至多是隐约感到有几只胸口发黑,仅此而已。
说实话,那种无力感就像2月6日的深夜里出现的感受一样。
不过,很快,我意识到:不只我一个人会产生这样的无力感,而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的心理状态,恰恰是这种无力感说明我们是正常的人;另外,也没必要为了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居然毫不管用而沮丧,因为哪怕再努力十五年也一样不可能有什么用。

想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看清一种鹑类的特征,是方向搞错了。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它存在的地方,寻求同伴的支持做好包抄,耐心等待,守到它自己慢悠悠地走出来,然后便可以将一切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它们果真不是棕三趾鹑。雌性棕三趾鹑的特征之一确实是胸口发黑,然而真相是这里生活着黑胸鹌鹑。感谢朋友圈里高手的提醒我才没有放弃,才能最终弄清楚真相。

棕三趾鹑属于鸻形目三趾鹑科,黑胸鹌鹑属于鸡形目雉科,亲缘关系遥远,基本属于八辈子挨不上的那种。但是它们的食物来源和生活环境类似,趋同进化造就了它们相似的外型、羽色伪装和习性。
这就好比制度会改变人是一个道理——再怎么不同的布料,放到一个大染缸里,出来的颜色都差不多。
天色渐晚,蒲甘皇宫的护城河遗址里荒草丛生,一株巨大的南洋楹长在早已坍废的城墙上,气势威严,如云华盖。我禁不住跑过去想拍几张照片。无奈逆光之下怎么都拍不出满意的效果,于是干脆爬进城墙内想找个顺光的角度,不料翻进去之后却被眼前的一切给迷住了。


夕阳下的丛林里,佛塔三三两两,以绝世之隐,藏了几多玲珑,几多精妙,几多让人看了意欲长住于此的魅力。宗教是艺术之母,建筑是凝固的艺术,这些佛塔此刻被树叶摩挲,被黄昏润泽,被飞鸟围唱,又被我遇见。
我站在那里很久,看着夕阳从佛塔身上一点一点收回金色的馈赠,佛塔渐渐恢复成灰白、砖红甚至墨黑的本色,可依旧是那么美!我承认先前的夕阳令它们看上去犹如圣光笼罩,但其实它们并不需要阳光的赞美,它们本身就是美的。

那些穹顶、那些雕塑、那些纹饰,它们源自于虚幻,成就于激情,又平淡于日常。它们早已不需要高高在上的威严来标榜自己,它们是可以触碰的、最真实的平凡。我赞美这种平凡。
那天的蒲甘,暮色如血,我的情绪久久无法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