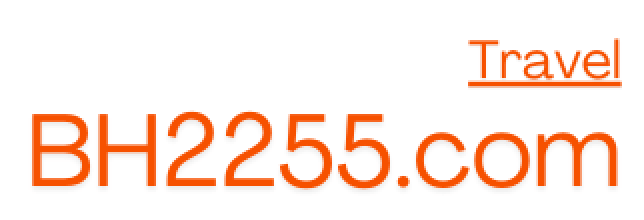在经过连续三天的跋涉后,人大登山队的队员们终于抵达海拔4800米的C1营地,即将于凌晨1点半开始冲顶。
这一天之内,他们要登上海拔5588米的那玛峰顶并返回C1,再立即下撤至海拔3900米的大本营。路远迢迢,跋山涉水,对身体和心理都是挑战。
8.6队记 三围
(一)出发
不知为何,这几个小时竟然睡得意外不错。可能真的是太累了,躺下就睡着,直到凌晨12点半被七秒叫醒。醒来时没有明显的高反症状,甚至有种我又可以了的错觉。
穿上厚衣服,套上安全带,扣好主锁牛尾上升器,费力的登上高山靴。看看时间还有富余,于是收拾了睡袋,把背包里不用的负重全部扔了出来。在考虑要不要带登山杖时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拿上(救我一命的举动)。
出帐篷觅食,半夜的C1还有些冷。想起狗哥说的穿衣厚度判断标准:站在外面等人觉得偏冷,动起来就正好。
今个早饭(实际上是夜宵?)是牛奶麦片,闻上去很香,喝了几口感觉还不错。然后,还没走回帐篷那就吐了……唉,以为自己不高反了果然还是错觉。
队长们随后宣布了AB分组,同时针管表示由于身体不适决定留守营地。作为针管的队医,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留下陪她。上山以来她感冒一直没好,还吃着药,需要人来照顾。临行前我也跟她保证过会随时关注她的情况。但一路走来,在这里就停下,自己当然是不甘心啊……此刻内心非常摇摆。
我问蚂蚁用不用留一个人陪针管,她安慰我说没事。听到阿狸还是谁问针管一个人留下可以嘛,针管也说没问题放心吧。好像终于给自己找到理由一样,在纠结后我选择了离开。后来知道针管很怕黑,更怕一个人待着,我们冲顶的那天晚上她并不好过。因此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很愧疚,怀疑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真傻,登顶哪有队友重要。
现在可以大言不惭的说愧疚,但当时的犹豫也只是片刻,回过神来,狗哥正在交待最后的注意事项。向导让大家再最后检查一下牛尾的绳子是否绑好。于是不少人又重新拆掉再打结。由于蚂蚁刚才已经帮我绑好了绳子。所以我只差把头灯固定在安全帽上,这时法海提醒我安全带腿环没翻过来,于是我又耽误时间重新穿了一遍。
 |
 |
临行前检查装备
本该前一天晚上就检查好的装备现在一个个都有些问题,狗哥很生气,为此训了蚂蚁,说为什么只说让检查却没有一个个的确认?蚂蚁也非常委屈,表示队员们不是小孩了,教过的、强调过的事情还做不好她也没办法。现在想来类似的事情不止一次发生,确实值得制度性反思。
经过一翻复查,大家全部收拾妥当。此时已经半夜2点,启程时间比计划晚了半个小时。

C1营地:印象派摄影师春礁作品
终于,在针管的祝福下,我们出发了。
(二)爬升
从C1上行,首先是一段坡度相对较缓的碎石路。海拔5000米已经是生命的禁地,白天时望向这边就是光秃秃的石山,夜晚头灯照射下更是看不到任何植被。

白天时远观那玛,远古冰帽下是大片裸露的岩石
由于休息不好加上落后于计划,大家情绪普遍低落,一路无言,就这么沉默的攀登。
状态不好的我还有阿狸跟着狗哥走在前面,速度不紧也不慢。走了一段后狗哥问我们节奏怎么样,不知为何,我竟然膨胀了说可以再快一点。狗哥给前面的宗翔哥和扎吉向导说了声,就去后面压队了。
随着坡度、速度、海拔的三重提升,能明显听到周围人和自己的喘息声。
呼吸频率加快,口渴感明显,嘴唇起皮,我应该是轻度脱水吧,我一边想着一边希望停下来补水。前面的路大概每20分钟停下来一次,但这时感觉时间过得格外慢,好不容易到了20分钟但路段有落石的危险不适合停留于是只能继续爬升。
追赶向导越来越吃力的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天真,表示狗哥老司机还是稳,控制速度实际上能让队伍走的更久更远,整体上休息次数和时间少了也更节约时间。于是在停下休息时我表达了希望降速的想法。
不知道是因为休息好了还是真的降了速,好像又能跟着往上爬了。但这时阿狸的状态却不太好,她高反加重走不动,感到恶心想吐,还出了很多虚汗。我们走着走着就从最前面掉队到最后面,路上时不时遇到需要手脚并用才能爬过去的大石头,体力加速消耗着。知道如此,但胃里难受就是吃不进任何东西,我们逐渐离大部队越来越远。
在后面赶路很累,前面人休息了我们还没到,终于到了休息点,但大家很快又要出发。蚂蚁从前面回来,陪阿狸在后面走了一段,建议她在最前面走。但阿狸体力还没恢复,在前面也走不快,队伍走走停停一段路后最终还是决定让一个向导(好像是丹哥)陪她走在后面。
看着阿狸头灯的光线越来越远,队伍便停下来等待。这时远处隐约闪着一个光点,大家反应了一会才意识到那是我们的营地,针管可能出来上厕所了?不仅感慨一个多小时才走了这么些距离(下山时才知道这段距离有多难熬)。
七秒拨通了对讲机,跟针管说了我们的情况,询问针管感觉怎么样。听到针管那熟悉的总结工作式语气,我稍微安心了些,赶紧叮嘱她少吃药多补水(也不知道她那边听到了没)。过了一会阿狸也上来了,狗哥问她感觉怎么样,能否继续下去,实在不行的话现在下撤还来得及。坚强的阿狸表示能继续走下去。
在黑暗中我们继续爬升,头灯照亮的只有眼前的路。行进、休息、行进、休息……就这么单调且重复的两个小时。右手边是隐藏在浓雾和夜色中贡嘎主峰,若隐若现。

远处被浓雾遮掩的贡嘎主峰

浓雾散去后白天的样子
在冰壁前的最后一次休息是在一个大平台上,四面透风,非常的冷。于是我准备在冲锋衣里加件抓绒,最内层的速干短袖早已被汗浸湿,一阵冷风吹来感觉身上仅存的温度都被带走了。赶紧套上抓绒穿上冲锋衣,贴着衣服感觉身体更加冰凉,又从包里取出最厚的滑雪服穿上,还是不停地打颤。
好冷。
我不会失温了吧,这还走到冰壁呢,我还没看到雪线就要下撤了吗。蹲坐在地上一边想着队医培训时的急救知识一边瑟瑟发抖。这时离我最近已经抱成一团的河妖与春礁伸出了援手,三人对坐抱在一起。但即使这样还是好冷,感觉整个人像是贴在冰柱子上。
这时不知是谁建议说吃点东西补充能量,才想起自己一直没吃东西(起来喝的几口麦片还都给吐了),于是忍着反胃吞下一块脆脆鲨和不知哪个好心人的果冻,喝了些快要冷掉的温水。然后没做停留就继续前进,过了一会后好像就没再觉得冷了。
(三)雪线之上
8月6日早上6点,我们终于抵达冰壁下面。眼前的冰壁大概五六十米高、坡度为70度。A、B组分两条绳分别上升。
走到这里,大家都有些怀疑人生。六老师接受法海采访时,发出了本次登山活动的最强音。
你为什么来登山?现在有何感想?
天逐渐亮了起来,大家开始更换冲顶小包,没有冲顶包的我扔下大登山包,带了大冰镐,把一个水杯放在河妖的防水背包里背上,这就是冲顶路上的全部家当了。
队员们依次爬上路绳,开始攀登这陡峭的冰壁。采用踢冰的方式可以较快上去,但如果只借助上升器加八字步的话会非常费力。向导们不停地对挂在冰壁上休息的我们喊“踢冰、踢冰”,但由于没有经历过冬训或攀冰训练,很多队员踢冰动作不熟练,还是不自觉地采用八字步向上爬,导致爬上冰壁花了较长时间。

冰壁攀登

冰壁之上
通过冰壁后是一段冰岩混合上升路段,好在坡度不大,且向导们早已铺好绳索,借助上升器可以较轻松地快速通过。就是走过最后一段没有绳索的冰岩路时有些战战兢兢,两边都是悬崖且没有保护,需要格外注意。

冰岩混合路段
现在,挡在我们和峰顶之间的只有眼前的冰雪路段了。
一望无际的雪坡像极了北方冬天的景致。不同之处在于,眼前的风景,静谧中透着危险。看似平坦的雪地下隐藏着冰裂缝,一旦掉进去便有生命危险。

沿着前方的脚印走倒也不是非常费力,但总会一脚踩空陷进雪里,浅的地方没至小腿,深的地方直接埋到大腿根。经常看到前面的队友突然跪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六老师雪坑救援
跪倒时伴随身体前倾膝盖会着地,另一条腿的高山靴有个侧翻动作,相当于自动上锁卡在雪里,人本能的想从最短距离直线拔出,但这样冰雪对靴子的阻力只会更大。在缺少支点的情况下想把腿从雪里整出来并不容易,每次都很消耗体力。三个月体能训练的成果,在这一刻纷纷得到了检验。
前行的路上难免会摔跤,但一跪再跪却是我始料未及的。抬头看前方,是那玛连绵的雪坡,但这时的我丝毫欣赏不来她的美感,只是想着翻过眼前的雪坡赶快到达峰顶。
然而爬上了这个雪坡,看到的却是另一个雪坡,蚂蚁和春礁紧跟向导走在最前方,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中。我只能尽可能地跟着前方的河妖和七秒避免掉队。

大雾中只能看到前方的河妖跟七秒
这时听到后面传来惊叹声,回头看,发现太阳出来,浓雾散去,贡嘎主峰露出了真面目。之前都是远观贡嘎,只有圣洁、美丽、静谧这些单纯的雪山刻板印象。但现在我竟一阵恍惚,她离我是那么的近,彷佛纵身一跃就能落在贡嘎的怀抱中(不是)。从雪线之上观贡嘎,确实是另一番景致。

雪线之上观贡嘎,人类是多么渺小
发呆间,晨雾再次遮盖住贡嘎,我们又陷入了白色森林。起身继续前行,七秒跟河妖已经走到前面较远的位置了,我得提起速度来。看到了美景似乎也多了分力气,可以在雪坡上继续踢冰。这样虽然比走路更费力,但可以有效避免踩空陷入雪中,实际上行进效率提高了不少。
我以百米冲刺的姿态缓慢前行,终于追上前面坐在地上休息的七秒,想着趁热打铁不如多走一段路再休息,无奈脚印两边都是白色的冰雪,偶尔透出一条深不见底的冰裂缝。
绕过去太危险了,还是慢点走吧。这么想着,人也松懈了下来,提着的一口气呼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迷迷糊糊间听见有人喊我,竟然是后面赶上来的姨妈让我帮他拍照。所以我刚才,是睡着了吗?竟然毫无意识地原地睡着,大概是大脑缺氧了吧。抬头看前方,七秒已经看不见了,我到底睡了多久啊。
“三围,三围,帮我拍个照吧!或者录一段视频也行。”小姨妈又喊道。啊对了,要拍照,于是我赶忙掏出手机,喘着气帮他拍了这段上坡的视频。
小姨妈爬雪坡
小姨妈心满意足地继续前进,我缓了缓也爬起身来向上追赶。
(四)登顶及雪坡下撤
登顶前的记忆已经过于模糊了,我也不记得爬了多久才到。到达顶峰时,没有想象中的登高望远,更来不及感叹大好河山。只记得四面环绕着雾气,什么也看不清。匆匆忙忙拍完登顶照和合照后,便要下撤。迷糊间防水包也还给了河妖。

表情僵硬的登顶照
上来那么困难,下撤应该能好些吧。当迈出第一脚就陷入雪中时,我便不再这么想了。下坡远比我想的要困难,一方面是坡度太陡,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我体重太沉,我每踩一脚都会下陷十厘米左右,稍微没站稳就会摔倒。

站着要睡着的样子,很容易就地摔倒
小姨妈拍摄的下撤视频,记录了美丽且危险的雪坡
后面学着重心靠后,用脚后跟发力,又总会一不留神整条腿陷进去。

拔出腿后留下的雪坑
由于体能状态不佳,我下撤时紧跟着扎吉向导和河妖走在前面,可是不受控制的一路摔跤,就这样离他们越来越远。
走着摔着,发现自己逐渐有些意识模糊,本来就小的眼睛现在几乎睁不开,随时都能睡着。于是下意识地喊前面几十米外的河妖,说如果我不小心睡着了就喊醒我。
河妖很无奈地回过头,说她在前面走看不见我啊,这话应该跟后面的人说。当时可能真的是糊涂了,连这个都没想到,回头望去好像还没有人过来,于是继续跌跌撞撞地往前走。
再次醒来时,只觉得口渴。水,好想喝水啊。水杯似乎在河妖那里,抬起头来河妖变成了远处摇摇晃晃的一个小点。
“河妖,我想喝水”,我坐在雪地上喊道,她好像停了一下,说了句什么我没听见。“你前面休息的时候等我一下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声音越来越小,或者干脆这句话只是停留在脑海里并没有真的说出。记不清了。现在想来自己那个时候应该很烦人吧,只记得自己想喝水完全没关注到她的状态。她当时情况也不好吧。
我缓慢地爬起来,想快点赶上她。听到后面似乎有人过来了,一看是法海和老保。在我看来,法海简直是户外大佬,体能装备技术样样行。
于是我用力喊道“法海我要是睡着了你叫下我啊”,法海半睁着眼似乎没听清,我又重复到“我现在有点意识模糊,要是走路不小心睡着了,麻烦你叫醒我。”法海还是没说话,动了动脑袋示意,那应该是听到了。
我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下坡,走到后面倒是没睡倒在地,就是打着瞌睡迷迷糊糊地往下挪动,隐约间听到耳边传来“别睡”的声音,可能是法海和老保超过去了吧,我点点头,继续打着瞌睡下山。又摔倒了,好麻烦,真的好困,我就睡一小会。想着抱头埋在膝盖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可能是一分钟,也可能是五分钟十分钟,丹哥在傍边喊我,“你睡着了啊?”,我眯着眼说“太困了,摔倒就能睡着”。丹哥没再说什么,很安静地陪在傍边。过了一会他说休息好了就走吧”,我点点头,想爬起来。

我坐在地上不想起来
结果没起来反而坐着往前滑了一小段距离,我用手撑着又试着滑了一下,顿时有些惊喜,这样移动很省力啊!还不用担心脚陷进雪里。我问丹哥可以坐着向前走吗?他说不行太危险了,还是要站起来走路。我不舍地爬起来,费力地继续下坡。
没走多久就又开始打瞌睡,不行不能这样,万一脚滑没摔进坑反而从“路”两边滚下去怎么办。摇摇头强制自己清醒,吸了口气开始“百米冲刺”:注意力集中在脚后跟,每一脚不会踏的特别用力,快速换脚,这样可以稍微保持平衡,然后一路小跑下去。
跑的跑的感觉有点停不下来了,于是连忙减速。果不其然,又摔了。而且滚了两三圈才靠冰镐制动停下,丹哥连忙从后面赶上问我没事吧,虽然摔得略惨但终于有个能下山的方法了,现在是跟时间赛跑,不拖累大部队,早点下去比什么都强。
爬起来缓了缓,走两步继续小跑,然后摔倒,然后继续。期间除了有次摔倒整条腿陷进雪里拔了半天才出来,其他可以说是顺利。丹哥由于要照顾其他人走到了前面去,狗哥这段路一直走在我身后压队,担负起了叫醒的重任。

雪坡将尽,下撤的战线已经拉得很长了
恍恍惚惚间,终于看到雪坡的尽头,这条无尽之路走的太难了。小跑到冰雪和冰岩的分界处开始减速,总算踩在了实地上。有些头晕眼花的走过无保护的那段“龙脊”,把主锁扣在路绳上时,才送了一口气。
弯着腰沿着路绳走,过节点,上保护,狗哥在后面拆站(我果然是落在最后面了啊)。走到了冰壁上,叹一口气,下去又是个费力的事,对于技术不娴熟的我来说,下降比上升要麻烦。
等候多时的扎吉老师看到我迷糊的样,顺手帮我套好了ATC,我瑟瑟发抖(这次是站不稳不是冷的了)的面向冰壁,两手抓牢保命的绳索,慢慢的放绳往下降。低头一看怎么还有这么高,手没有力气了得赶快下去,于是想起云梦峡攀冰时的速降,想要快速放绳跳着下去(又膨胀了),但跳了两下吓到了下面的向导,于是最终还是老老实实的降下来,找到一个石头立马坐下抱着自己打盹,陷入了自闭状态。

陷入自闭状态
(五)无尽的碎石坡
大概就这么休息了10分钟,又要出发了。由于反应迟钝,没来得及跟上第一波下撤的伙伴,拖着大背包走在后面。六老师也一脸疲态,但看到我的衰样还是帮我分担了大冰镐。
记不清几乎直上直下的那段岩石路是怎么下去的了。
悬崖峭壁碎石坡,上来不容易下去更难
灌满冰雪的高山靴把脚磨得生疼,每走一步路腿都在发颤,最糟糕的是我仍处在随时要睡着的状态,眼睛困的睁不开,甚至开始出现幻觉(也可能只是边走路边做梦):我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井一样的池塘中,能看到岸边的树和人影晃动,但就是爬不上去也够不着。
睁开眼睛周围却是清一色的岩石,脑袋很沉没力气抬头只能低头看着脚下,弯腰撑着登山杖才没有摔倒。
不能睡啊,我要快点下山,到了营地就能休息了。一边想着一边摇摇晃晃跟着前面的人走,走的一急又摔倒在地。熟悉的剧情再次上演,趁着摔倒我抓住机会打盹,直到被后面的人叫醒。
至少坐在石头上睡觉相对安全些,不至于失足摔下悬崖。但一路上磕磕碰碰,继续即使穿着几层长袖和冲锋裤,胳膊、手背和膝盖还是陆陆续续的擦破了皮,右手两个手指的关节流出了血。碎石坡的难顶之处就在于此,摔一下就是伤,不像雪坡摔倒软着陆只是爬起来费力。
太累了,头好晕,又走不动了。狗哥在后面催促,说什么海拔降下去高反就好了,可问题是我怎么才能走到下面啊……
当时确实太累了,绝望中还有些委屈,那时候感觉只有针管才能理解我的感受。想给她打电话,让她开处方告诉我该怎么办。我用登山杖撑在原地(实在没力气坐下了),掏出手机,看到移动和电信都没有信号,但还是拨下了针管的电话。果然,打不通。好吧,我死心了,小脾气没了,咱继续走吧。
也不知道当时我走的速度有多慢,反正每一步都摇摇晃晃,走两步就要休息几秒站稳。现在判断应该是中度以上高反,连串联行走测试都完成不了。
本以为幻觉/走路做梦是高反症状的顶峰了,可突然的一阵环绕型头痛让我体会到什么叫折磨,前一秒还在池塘里打盹,下一秒就感觉脑袋被几十根针扎一样的疼。我抱着头,疼到眼泪都流了出来。老保赶忙从后面跑过来问我怎么了。我那时有点说胡话了,喊着“好多针管,好多针管在扎我”,留下老保在一旁手足无措一脸懵。唉,我上来时都没这么难受啊。
保老师其实从昨下午到C1一直难受到现在,可看到我闭着眼走路还是不放心,伸出手说要扶着我走。无奈我体重是他的1.5倍,他这么一扶两个人在碎石坡上一起摇摆,太危险了。我那时虽然离傻不远了,但这个常识还是有的,于是继续拄着拐慢慢挪动,三步一晃,五步一摔。真的苦了陪我在后面的狗哥和其他几个人。我耽误了大家这么多时间。
刚才还隐约看到春礁在前面的山头,她是我的队医,手上的擦伤想先找她处理一下。小急救包被我放在了营地,B组药包不知去处,A组的医药包可能在春礁那里,给几个创可贴包一下手就行,如果有补液盐什么的更好,虽然现在早已喝光了最后一滴水,就这么想着,抬起头时却看不见他们了。

转眼就消失在山间
春礁和扎吉向导他们分明刚刚还在视野里的啊。我不由得怀疑自己是不是迷糊中又睡着了。我大喊了两声春礁,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可能是已经走远了吧。
只能继续往前走,想办法在休息时赶上他们。但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往哪儿走?
前面的碎石坡曲曲折折,根本不存在“路”的概念,他们是从哪个方向拐弯了呢?现在难道要雪上加霜,在乱石岗上迷了路?第一反应是回头问狗哥,但狗哥竟然在后面老远的峭壁上。看看周围的六老师和老保,也都昏昏欲睡,只有法海还强撑着,往高处爬,试图定位和找路。
我们就这么边摸索边走着,终于在翻过一个山头后看到另一个山头上的他们。无奈相隔太远,一群老弱病残一时半会也过不去。他们等待许久后,留下小姨妈给我们指路,其他人继续赶往营地。我们则在法海的带领下,向他们之前所在的平台推进。
关于这段路的记忆实在是太过模糊,只记得自己摔了很多次,越走越慢。狗哥让法海先回营地找人来接我,六老师、老保也相继离去。
之后狗哥陪着我走了很久很久,也没见有人过来。这时候隐约可以看见远方的营地,但不见法海和老保,六老师坐在山脚的一块石头上,似乎很不舒服。狗哥有些担心法海他们的情况,另外当时好像有些变天,狗哥判断了一下我的状态,说是再走一个半小时也到不了营地,需要在下暴雨前找人帮忙才行。于是留给我一根登山杖后匆匆离去(我的另一根借给了六老师)。

下撤的碎石坡,摔起来更疼
啊,现在山上就剩我一个啦。我停在原地调整登山杖的长度,望向前方,隐约可见有两面做标记的小旗子。路的坡度好像也不是很大,像丘陵一样,似乎一溜小跑就能下去。于是又有了些信心,便沿着狗哥下山的路前行。
可是走了没多少米,便再次感到一阵眩晕,多亏两根登山杖撑着才没摔倒。努力睁开眼睛,想迈出脚,但眼前只有20厘米高的石头却像悬崖一样跨不下去,我这是怎么了。用登山杖撑着,侧着身子迈出脚步,才勉强走下这块石头。可是眼前还有无数的石头等着我。
就这样,走三步路停下来,闭上眼睛大喘气。这副样子可能远处看来跟一动不动一样吧,我看到山脚下的六老师站了起来,对我喊话。可是太远了,我的意识也很难集中,完全听不到他说什么,只能晃了晃登山杖示意。六老师又坐在原地抱头,不知道是不是也走不了路了。狗哥下山的路线应该会经过老师所在方向,至少能看见他,所以六老师暂时是安全的。
停在原地不动头脑至少还能思考,但一走路就晕了。走了几步后我坐在地上休息,鬼迷心窍地又想起雪山上的滑行移动,碎石坡上很多石子,确实也能滑,但坐着硌得慌,登山杖太细也没办法随时制动,只有在下陡坡的时候才能用得上坐姿。乱想了一番后还是爬起来继续走,身体很痛苦但大脑依旧话痨。
心里想着我是不是已经习惯这种一小步一小步地龟速移动,所以本可以走快也因为思维定势或肌肉记忆(又乱用词了)走不快了?刚想着试试走快点,就摔倒在路旁……虱子多了不怕痒,摔得多了不嫌疼,拍拍脏的不像样的冲锋裤,爬起来继续走。
可能就这么走了两百多米,拐入一个坡道,看到了之前误以为的丘陵。原来是坡度近40度的乱石岗,山上看起来它分明还那么平。大石块正常情况下或许能爬过去,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无异于登天,于是只能沿着相对平缓的小路绕着走。坡上的碎石越来越细,稍不留神就会滑倒。让我想起初中物理学的“变滑动为滚动,摩擦力减小”。正想着,天上开始下雨了。
不对啊,这雨点怎么这么大,砸的人脑壳疼?用手一接,发现原来是冰雹。说实话,当时的我是有点新奇的,毕竟第一次接触到冰雹:半透明、椭圆形、有一定厚度的片状冰。不愧是雪山,虽然光秃秃的没有植物,但气候还是多样啊。兴奋劲儿过去后,也开始有点担心:这漫山遍野的碎石头,也没个躲雨(冰雹)的地方。
这时忽见远处两个人飞一样地走来,一个是嘎玛大哥,另一个看着有点眼熟但不晓得叫什么。这就是救援队吗,他们准备怎么带我走呢。
他们快走到我面前时停了下来,问我能走路吗。我说能走,走不快,站不稳,老摔跤。听罢其中一人走近把我胳膊搭在他的肩上,拖着我往前走,另一人无从下手只能在一旁护送。
这段体验该怎么说呢,我的前行速度一下子快了10倍不止,但脚上的疼痛也倍数增加。本来迈不动腿的我,相当于被拖着前进,小腿微曲(不然就是我搂着两位大哥走了),高山靴不断撞击着地面,开始还能闷声忍着疼,但后来大哥们嫌速度慢,于是一左一右架着我,在碎石坡上飞奔,我已来不及感叹二人的体能和翻越乱石堆的灵巧,等到速度加快路上只剩下我“疼疼疼疼疼疼疼,嘶,哎呦”的声音。后来隐约记得两人只停下休息了一次,换了位置然后继续架着我奔跑。
就这样,我可能几个小时也走不完的山路,在大哥们的帮助下15分钟走完了。
(六)C1下撤
回到本营时大概是下午3点半,我们凌晨2点出发,8点登顶,而我下撤竟然用了比冲顶还要长的时间。这时大家已经在收拾东西,准备拔营了。
我识相的没有钻进帐篷,找到一块绑防风绳的石头坐下来休息。此时完全没有力气去拆帐篷,最后是阿狸春礁还是谁帮忙收拾好的,在此感谢她们。
当费了好几次力才脱下湿透的高山靴时,发现右脚踝后侧磨出了半个巴掌大的水泡,傍边还有两个小的,左脚的大拇指由于淤血变黑了,鞋里还倒出了一些碎石子,不知是融化的冰块里的还是摔倒时漏进去的,难怪一路上脚疼了……
协会的高山靴最大号的就是这两只,左脚44号,右脚43.5,去年去云蒙峡攀冰时就穿着这双混搭鞋,但没有走这么多路所以还好。唉,等赚钱了一定要给协会捐装备,至少鞋子得整成一个号的。
正做给协会更新装备的梦,针管走了过来,用她那2L的超大保温杯给我倒了一盖子热水,看着我喝下去,还给我一只葡萄糖注射液让补充能量。呜呜,看到针管忍住不哭。喝水补糖续命后,起身去收拾登山包和驮包。一路上我都在嫌弃这个登山包沉,但多少次摔倒都是包先着地保护我。唉,拍一拍它,这个包跟着我也不容易。
由于水泡太疼,为避免压迫伤口我最后还是穿着凉鞋下撤。从顶峰下来约800米的海拔后,又补充了水和糖分,我终于可以正常走路了。虽然一瘸一拐走不快,但至少没有头痛欲裂和意识模糊的症状了。
下撤拔营时,由于行动依旧缓慢,还是被落在了后面。跟我一起走的是六老师,法海和蚂蚁走在后面压队。望向前方,可以看到阿狸春礁两个好兄弟走的老快,领先我们一个山坡的距离,老保跟在他们后面不远处,孤独地前行。再往前的队友已经看不到了,真羡慕他们的体力和状态。
慢慢的,法海赶了上来,蚂蚁也走过来问我状态怎么样。就这样,我们一行四人以相对稳定的速度行进。先后路过了昨天上来时的溪流和高山草甸,昨天从这里路过时,脚下石洞里突然窜出的土拨鼠还吓了我一跳,今天没有再见到这位小老弟。

遥望本营——上图中间浅色的草地
我们沿着下山的路走啊走,六老师不时地转过头来问我怎么样,还能走动不。还说要帮我背包,轻装上来的他下撤时分明已经背着阿狸的包了。啧,自从被从雪坑里刨出来后,独狼六老师也这么会关心人了哈哈哈。
蚂蚁一路上放着音乐,多数是纯音乐,也有一首有歌词的,蚂蚁嘟嘟囔囔地唱着,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魔性又洗脑的旋律陪伴着我们的下山路。
走到半山腰时,我们看到山脚河边的阿狸和春礁被返回来找人的宗翔哥接走了,但老保还不见身影,蚂蚁担心他一个人迷路,于是先下去找人。我和六七、法海三人继续以老年组的速度移动。
走了没多久,我们三人都不由得停了下来。不是因为劳累,而是看到了贡嘎。贡嘎露出了山尖,雪顶以下全部被云雾包裹着,看上去就像是飘在半空中一样,“贡嘎神山”,脑海中冒出这四个字来。
这是我第一次认真的看贡嘎,其他时候不是在赶路就是被云雾遮挡,在号称最佳观景平台的那玛峰顶也只看到一片白雾茫茫。虽然现在已经傍晚7点多了,太阳即将下山,但我们还是不由得驻足,拿出手机,试图记录这一幕景象。

漂浮在半空的贡嘎神山,相机拍不出她的美
再往下走,水雾蒙蒙中飘起一面竖长条形的白旗,像是放大数十倍的哈达,垂在对面的山上,从山腰一直到山脚。旗下是两顶白色的帐篷,若隐若现。当时我就想到了《千与千寻》里的雾中小镇。
“这是海市蜃楼吗?”我问道,他们俩沉默着没有说话,我们又呆呆地看了一会,分不清楚是真是假。
继续往下走,距离山脚更近时发现帐篷边上有两匹马,似乎有人在交谈。“这就是蚂蚁说的老本营吧”,我喊道,离我们的大本营应该也不远了。
感觉又走了好久才到山脚,眼前是段涉水的路,水流湍急但并不深。我们过了浅滩走到帐篷旁看到了蚂蚁和老保。我想今晚要是能在这休息也行啊,天已经黑了,赶夜路太不方便了。蚂蚁说她刚问了嘎玛大哥,今晚结算马拉驮包的费用,看能不能顺便骑马回去。听到这里我心放了下来,老马识途,我们马上(真的在马上)就能回到营地了。
此时肚子已经咕咕叫,想起来这一天几乎什么都没吃。脚上的伤也没来得及消毒处理,我心里盘算着一会到了营地要做的事情。
在帐篷门口等了一会,也没见嘎玛过来,我们猜想他可能牵马去了。帐篷里已经住了两位大哥,准备明天冲顶,看我们在寒风中站着赶紧招呼进帐篷里取暖等候,还给倒了热水喝。坐了一会,天色越来越暗,蚂蚁说我们在路口去等吧,于是跟两位热心大哥告别。他们把我们送出帐篷,看我们走远才进去。其中一位还一直劝我说晚上天冷换上登山鞋。
我们沿着河往前走了一段,也不见嘎玛大哥过来。天色越来越黑,需要打着头灯才能看见路。由于蚂蚁手机没信号,所以用我的手机给嘎玛打了个电话,希望他能给我们带路。不一会远处亮起了手电,我们也用头灯和手机灯回应。嘎玛大哥只身一人稳步走来,看来终究还是没有等到他的马哈哈哈。蚂蚁叮嘱了一句嘎玛走的很快,让我们一定要跟紧。看我没有头灯,就分给了我一个头灯(后来才知道那是六老师的,六老师一路上都没有灯)。
嘎玛大哥过来后,告诉我们一会穿小路过去,大概需要35分钟(或者是15分钟?)风大水急,没有听太清楚。他又看了一眼我们,说带着你们的话大概50分钟能到。
唉,还要走50分钟的夜路啊。没等我反应过来,嘎玛就沿着河边大步向前去了。我跟法海跟在最后。由于岸边就是林子,只有很小的一条通道能走,我穿着凉鞋总是时不时的踩入水中,海总似乎不忍心弄湿装备,走的比较小心落在了后面。眼看前方的头灯忽闪忽灭直到消失,我有些着急于是喊到等一等我们。翻过了一个小坡看到蚂蚁他们停下在等待。我们刚出现,嘎玛大哥就又往前走了,蚂蚁担心我们跟不上走失在雾中,于是来到后面压队。
走在峭壁间的时候我又有点站不稳了,看路也比较模糊,差点摔到山下的河里去,把蚂蚁看的心惊胆战的。我爬起来后看她单手握着两根登山杖,另一只手拿着手机照明,问她头灯呢,她说给老保了。我就说你这样不行,走在最后还没有灯太危险了,你戴着头灯走后面我在前面也能看到。没想到蚂蚁顿时就发了火(瑟瑟发抖),说我戴着头灯走路都不稳,不戴更让人操心。我一想也是,身为总队长,队员安全是她最大的压力来源,便没有再提。
后面随着路况变得更复杂,我的状态也越来越差。走路摇摇晃晃,跟不上前面的人,经常走错路。明明有相对平缓的小道,我却没看到,绕路爬乱石岗。在又一次跟丢前面的人后,我跟蚂蚁说要不我跟着嘎玛大哥走前面吧,她喊停让大家等待,并拜托嘎玛大哥帮我背包。换了位置后,我后面是六七跟法海,老保、蚂蚁在最后。
跟着嘎玛大哥走没那么恐慌了,但也不轻松,挡路的树枝、河水上的石头、岩壁上的小路……无论遇到什么障碍他都不会减速,像是开了穿墙的金手指,刷刷的向前走,甚至相当长的一段路都跟朋友在打电话唠嗑。
而我在后面,极力追赶他的步伐,不时回头看看后面的队友跟上来没,有的路如果不看前面人怎么走是很难通过的。经常忙于追前面的嘎玛大哥,我再回头时看不到一点光线,就非常着急。只能不停地喊大哥停下等一等。后来嘎玛大哥等的太无聊,竟刷起了视频(不知是网速好还是提前下载的)。我一路上不止一次的怀疑自己不该走前面,即拖累嘎玛的速度,也没有给后面队友带好路。
最尴尬的是路上有两次摔的比较重。第一次被树枝绊倒,倒栽葱式地倒在路边的树丛里,被树枝卡住,听着下面传来河水击打石头的声音,多亏嘎玛大哥赶回来拉我起来。还有一次踩着石头过河时,脚下一滑,双膝跪进水里,一只手的登山杖飞了出去。由于水流比较急,我担心杖被冲走,赶紧喊大哥先去救杖,但大哥不愧是大哥,淡定的拉我起来后跳过石头取回了杖。
后面大哥可能感觉我这个脚滑型选手不太靠谱,有意识地控制了速度,走远了就自己停下来等我,还回头用手电给我打光照路。大哥一路上都很沉默,只说了句还没吃晚饭。我心领神会,说那正好一会到营地了一起吃,大哥淳朴地笑了。
走了大概1小时50分钟,终于看到了灯光,也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欢呼。啊,是队友在等我们。顿时特别感动,想赶紧看到他们。但走出林子后才发现眼前是一条又宽又急的河流。河妖在对面招手,扎吉老师和宗翔哥好像也在。
跨过河就到家了,我一边想着,一边用登山杖试探水深。水流的力量很大,差点带走插在河底的登山杖,但营地就在眼前了,怎么都要过去。我穿着凉鞋也没什么顾虑,挽起裤腿就下了河。水流冷的令人没有知觉,但右脚的伤口却刺人的痛。抵住水流的冲击,勉强站稳后,我先渡过了河。
夜晚渡河
蚂蚁由于身体不适,不宜接触冰水,最好有人能背她过河,但向导们说水太急了,背人的话两个人都有危险。无奈,蚂蚁在法海的搀扶下只能淌水过来。嘎玛大哥换上扎吉老师给准备好的雨靴,同时背着我和蚂蚁的登山包,也过来了。接着是老保,由于六老师没有带换的鞋,最终决定赤脚过河。
至此全员不怎么顺利但最终平安地返回到大本营。
ps.晚上吃了麻辣鸭和土豆牛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