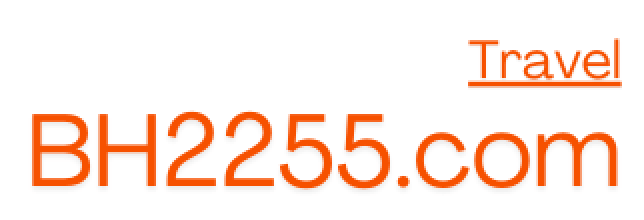对大理的特殊情感
于2020年10月19日

对大理有种特殊的情感。
每当我仔细思考这种情感的缘由时,想着想着,思想却像断了线的风筝,径自飞得老远,没留下一丝痕迹。以至于反倒令我讶异:刚才我是在思考什么来着?于是收起风筝的线,悻悻。
上学时曾无限憧憬一个人的旅行,有许多令我神往的目的地,想在学生时代把每个地方都去一趟,可终究还是作罢了。至于原因,说起来也颇为破坏意境——因为没什么钱。工作后有了点小积蓄,想实现当初的愿望时,却发现那样的神往近乎消失无踪了,对旅行的期待也没有那么强烈了。人好像很难在对的时间恰好做着对的事,时间这东西,总是那么尖酸刻薄。
去年年末,我头脑一热,辞去了薪水不低而清闲的工作,经历了考研又放弃、创业失败和疫情阴影下戎马倥偬却又满是空白的大半年后,5月底,我去云南曲靖去找朋友寻找重新创业的机会,最终这件事也未获成功。我决定在回家之前,去一趟同在云南省的大理,说走就走,决定离开的当天晚上就到了大理古城。
最初对大理的期待甚少,以为那是一座被风、花、雪、月四大网红景点过度炒作并且扭曲了的城市,以为它已失去了本该具有的特色,但当晚我就发现,是我错了。古城满是健谈又淳朴的人们,颇具特色而并不漫天要价的小吃,以及自然而然浑然天成出的超然气质。那天,不论是那个不由分说地非要请我喝酒的烧烤店老板,还是热心到甚至有点啰嗦的民宿姐姐,都让我长长地舒了口气:这座城的古朴还在。



那些天,我一个人租车绕着洱海转了两大圈,路边是久违的庄稼地和农忙人,路上大多是来旅行的匆匆过客。这样的碰撞让人遐想:我们心中所谓的远方,也正是困住身处远方人们的牢笼吧。路过喜洲和双廊古镇,满街白族特色的建筑和吃食,的确热闹。可相比于镇子,还是街边的农田和农民更吸引我驻足,那里有生活的迹象,有痛苦,也有希望,有与我既往生命相称但又辟开一段距离的种种,于是共鸣着,却也新奇着。



离开大理前一天的那个晚上,一个人吃了一桌菜,喝了一壶玫瑰酒,达到了喝酒的人们谓之微醺的最佳状态。于是借着酒后的豪情,拿着相机和三脚架,从古城穿过大片的野路,步行四公里多,就为了看看夜晚的洱海。那条路很窄,两旁都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开始的一段路有些灯光,接下来就完全是黑路了,没有路灯,唯见皓月当空。一个人走在似乎只属于自己的小路上,心中默念着“举杯邀明月”的佳句,感到无比浪漫,那种浪漫是带着些许孤独的,但也正因为这点孤独,又使得这浪漫生出几许骄傲来。在这环绕周身的侠气里走着,在空无一人的小路上走着,谛听农田里偶尔传来的悉悉索索的声音,浪漫而孤独,孤独得不可一世。走着走着,许是酒精消化殆尽,尚未成型的理智告诉我,这无垠的黑暗里也许会有狼啊,这偶尔经过的一两个人也许会有抢劫的啊。于是,已经走了一半,没有退路的我,带着浪漫、孤独以及些许恐惧走完了这一程——这么一回忆才发现,果然旅行中并非全都是美好,比如还会有些提起都有点丢人的恐惧感,只是善于闪烁其词的回忆,将一切滤掉了,只剩下美好的以及浪漫的。

总之,我终于看到了日思夜想的,夜晚的洱海,那晚,洱海边只有我一个人。支起三脚架,拍照一会后,来了一对四五十岁的情侣,从举止一看便知并非夫妻。看到我在这,他们心里肯定是有不快的,而我竟有一种不知所起的开心,好像他们的到来,将我摸黑走过来的笨拙举动合理化了,一种微妙的默契在我和他们之间构筑起来,同时或许也缓解了我的孤独感以及——刚刚褪去的恐惧感。看我拿着三脚架,他们请我帮忙拍照,那夜风很大,所以给他们拍的照片无一幸免,全部拍糊了,多次调整仍未果,但他们仍然感谢我。两人一定都喝多了,男的握着我的手说着愤世嫉俗而毫不设防的话,女的也言辞放旷地和我聊着毫无头绪和逻辑的天,大意似乎是夸我好、谢谢我什么的,女人说话时不住地望向男人,眼里充满爱意。陌生人向我吐露心声,我太喜欢那样的感觉。我已经无暇去思考,为什么女人特别想要照片,而男人偏不让我把照片发给他们;男人的妻子此刻在家做着什么,男人又是以怎样的借口瞒天过海;家中的女人和洱海边的女人对这个男人的爱又是多么悲哀……那个夜晚,我失去了所有的是非。只当那是复杂生活里抽出的一幅画卷,挺美的,况且真正的美,本就是掺杂着悲凉的。如此罢了。也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各种人各种生活展现在我的面前,好的、坏的、富足的、穷厄的,一切都无需评价也无暇评价,心中装满了山海才会真正知道山海也不过尔尔,心中盛得下各种美与各种丑,才会知道如何活得更漂亮。
话说到此,那晚的我已成功地搭到车回古城了,一切圆满。而此时在电脑前的我,那根思想的风筝线又断了——对大理的特殊情感的缘由,又失了踪迹。那种情感,也许就源自那晚走夜路的孤独和恐惧,和与那对情侣的偶遇吧。因为孤独所以浪漫,因为恐惧所以产生心理依附,因为那对情侣所以觉得那段旅程五味杂陈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