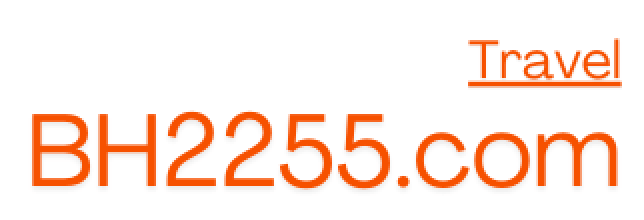朱毁毁的摄影展。
颇具趣味的文字有精彩思想。
蜀地,他称为“中国的中国”;
午后晒太阳的人,他称为“向日葵”;
微笑的汉代雕塑,他称为“群体性乐观”;
“花边棉被”——和棉被质地通感,厚重的云层和雾气是成都的灰色棉花,那些温和的城市棱角是这床棉被上的花纹;
“市场与水井”——所谓市井,前者流动、混乱,后者固定、秩序;
“茶水场社交”——饮茶在这座城市与茶道的关系是极其微弱的,它只是一项公共生活中的手段。



尤其喜欢这三幅作品,我称之为:
在历史前相拥-奋力根植浪漫-饭桌日常与光影奇幻
但真正给予我思索的,是这一幅:
在一片梦幻光影中,古蜀文明以镜像的方式呈现在现代人的脸上。
滚烫但柔软的金属液体被塑造成型,三千年后,它与最现代的符号“手机”晕染在同一处。强烈、重叠又暧昧的时代感。
古蜀两个字,有切断、湮灭、神秘的意味。与此对应,手机是连接、定格、信息过剩。

此前也有关于古蜀的体验。2019年盛夏与最要好的朋友同游金沙,站在象牙堆与流水般的乌木前,回头见到地层:

好友刘怡说,万世千年不过几十公分。
烈日、盆地、云层使我们皮肤粘腻,渴望饮冰。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见到三千年前巨大的榕树根,足有百余平米。而那时,成都平原的气温比现在还要高2-3摄氏度。实在无法想象,要如何忍受这份炎热。
苍天的榕树,提供信仰,提供阴凉,提供榕树社交。我想象古蜀人也似我们这般,脚踏尘埃,与友人并肩,一同获得着奇妙体验,那是群体最初的珍贵记忆。由此觉得非常亲切。崇拜树木,这多美,多亲切。
要再引一遍赵广超的文字:
“话说红拂女初遇李靖,眼见如此英伟真男儿,当下自剖心迹:‘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
“中国人本就径将一生托乔木。”

还有想说的话:
一,从友人罗阳处知晓朱毁毁。对“城市”“情感”有执念,屡屡穿梭在成渝两地,用许多精力去感知。似乎友人也是这般。读到极好的句子,与他共享:“即便走到天涯海角仍与自心同在,任何旅途不过是行走于个体的经验当中。”
二,展览现场布置优美,数位女孩儿在飘逸纱布前拍照。看展的人被拦下,因妨碍其拍摄被呵斥,理直气壮。她们在展览里看纱布、和道具互动、发表自己的观后感、购买衍生产品,唯独不看展品。她们已经走到此处,在朱毁毁的作品前本可以获得更多。就差那么一点儿,好可惜;但对展览行业来说,走到此处已是不易。漫漫长路。
三,观展结束后,从宽窄巷子步行至柿子巷。本有捷径,奈何门卫固守阵地,慌称胡同死路一条。绕行极远,终于到达胡同另一端。这次看得分明,小巷穿堂而过,不过数米。心有不甘。因疫情、安全等缘故不许通行,倒也能够理解。但欺骗拙劣。
绕行途中,见餐桌齐整地排列在街头,收购废品的老者步伐不稳,他想把桌上的菜单拿走回收,老板匆匆奔赴阻止。一方呆滞耳背;一方大声解释。并非不明事理,只是被发现了。
巷口有明镜,光影极美。是辟邪吗?母亲摇头笑道,是剃头匠的物件。她还说,看啊,草木在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