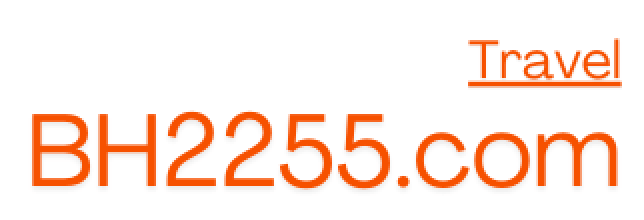十一假期我和阿郝前往川西短途自驾旅行。这是从春节之后我和阿郝第一次离开北京。关于远行的未来一切未卜,只能珍惜眼前每一次可以探索未知世界的机会。如果说「疫情」带给我的影响和思考是什么,那这想必一定是其中之一。
从成都到海螺沟,大部分路途都是平坦的高速,山体内的隧道绵长,仿佛要开到地老天荒一般。不过,自驾旅行伊始的喜悦冲刷掉了这些本该令人煎熬的过程,我坐在副驾上四下张望,一朵盘旋在山腰的云都能带来极大的赞叹。

海螺沟是成都周边久负盛名的冰川公园,对于国内旅行极不了解的我,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我们在将近中午的时候抵达,穿过景区门前的磨西古镇。这是一座街面已经被完全整修过的「古镇」,拥有着崭新而高度统一的临街房。一条笔直向上的柏油马路把游客引向海螺沟的入口处,在这里,还要换乘一趟上山的观光巴士,才能抵达景区观光的真正入口。
车程大约需要40分钟,司机驾驶技术娴熟,越过一个又一个发卡弯,把我们带向山之腹地。我和阿郝在「三号营地」下了车,预定的「摄影酒店」便是在这一站。海螺沟内观光巴士停靠的站点名令人迷惑,但说来也简单。在发现贡嘎山以后,前往此处登山者的营地成为了本地命名的来由。一共四处营地,由远及近靠近冰川深处。「三号营地」是倒数第二处,住宿在这里的话,可以在清晨看到「日照金山」的胜景,当然,前提是天气足够好。

🏔️
放置好行李,我和阿郝决定前往四号营地,再行登山。天空开始飘起细密的雨丝,2900米海拔对于平原来客的影响也开始显现。才走了几级台阶,就觉得头疼得仿佛脑子要和脑壳分开了,我们转回身到巴士站等待上山的下一班车,几个弯道以后,司机把我们送到了景区公路能抵达的最高处。
比我们早抵达的游客拥挤在缆车的售票处前,一问才知道,山顶的天气大雾弥漫,即使上山,也完全没办法看到冰川。
「如果你们想看冰川,我建议你们明天再来。但是如果你们就是喜欢坐缆车,那另当别论。」坐在售票窗口里的工作人员隔着玻璃窗对我说。我忽然想起几年前在蒙村的Mont Tremblant,我们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同样是在售票处被工作人员劝退的。命运真总是惊人的相似。
「那……」我有点儿犹豫,把问题抛给了阿郝。
「这个季节天气总是这么不好吗?」阿郝问工作人员。
「高山上的天气谁说得好。」工作人员说,「你们应该冬天来,冬天山顶风大,什么雾都能吹散了。」
「冬天还能进山吗?」我不知从哪儿来的常识以为,这儿到了冬天会封山。
「当然能了。」
我看看阿郝,我俩通过眼神确认了冬天再来的可能性约等于零,于是他很坚决地说,上山,明天的天气也未必好。
工作人员对他的推测不置可否,递给了我们两张缆车票。缆车站前除了兜售雨衣的藏族商贩和穿着黄色背心的工作人员外,只有我们两名游客。原本该挤进8个人的缆车被我们独占,这么晃晃悠悠地向上,进入了深深的云雾中。


工作人员说得没错,此刻前往山顶的路上,都已经被云层所包围着。我们跟随缆绳的前进,匀速进入了云中。那些曾经在飞机的舷窗旁幻想过的「站在云顶」的幻想,此刻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云的内里明亮,但空无一物,我们产生了一种「当离开云层的时候,不知外面的时间是不是还是2020年」的想法。
缆车的窗户打开着,带着细密水雾的风灌了进来。无法判断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水流还是风的呼啸。我们只能静静等待着抵达终点的时刻。此时距离地面有多高,不知道,距离山顶有多远,不知道,前后的缆车在哪里,仍然不知道。我想起《哆啦A梦》有一本长篇故事,大雄前往宇宙中另一颗星球的路径,就是穿越一片粉色的云海。不知是不是因为藤子先生和我们经历了同样的旅程,才会画出如此贴切此刻心境的故事来呢。

抵达山顶的时候,并没有像山下的工作人员说的那样,下着「比山下大很多的雨」。每一座观景台周围,都笼罩着浓重的云雾。本应该近在咫尺的冰川与山脉消失不见,我甚至没办法判断,它们是在观景台的哪一个方位。我此刻在海螺沟的山顶眺望,而这些云雾倒让我可以以为我在任何地方。
每个人与此处冰川的初见只有一次机会,这样的画面,我倒并没觉得失望。
🏔️
步道两旁生命力茂盛的植物成为了我和阿郝仅剩的可欣赏的风景。这是一片仍保留着风貌的原始森林,溪流、枝丫、苔藓、落叶、死去的枯枝、再度生长出的细小生物,森林拥有着自己的法则来诠释生命的流转,包容一切生命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找呼吸的法则,尽管这里寒冷、多雨、阳光稀少、阵风强劲,但是它们仍然生生不息,顽强地绵延。
相对于原始森林,以及不远处的冰川,我们在此刻的相遇不过是一瞬间。不过,宇宙就是由无数这样的瞬间组成的。叶子在秋天离开树枝的一瞬间,植物破土向阳的一瞬间,死去的树木扑回到大地的一瞬间,水流越过岩石冲向悬崖的一瞬间,冰川凝结的一瞬间,我们的目光停留在它们身上的一瞬间。
去年在挪威的峡湾,我也遇到过冰川,对于这些百万年凝结的奶蓝色巨大冰体,我感到自己的存在前所未有的渺小。那是一处叫做Nigardsbreen的冰川,抵达的时候,整个山谷只有我和阿郝两个人,我们和冰川隔着湖面相对,距离不到200米。我想到冰川变成冰川的时间,要从此刻向前回溯几百万年的时光,那个数字太过于庞大使我失去了概念,那个时光太过于遥远使我无法想象。它们百万年来都凝固在此处,而我,跨越千山万水与它见了一面。
这似乎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
此刻,亦如当初。🐑






这篇文章的原文在旅行中我po在了另外一个随手瞎写东西的小号,受限于原创内容管理的限制,没有办法把原文重发。修改了措辞,但是故事是一样的故事,必是的想法沉淀到一周后的今天,也是同样的感触。
公号系统强大的原创保护机制,瑞思拜。
对此带来任何不好的阅读体验,鞠躬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