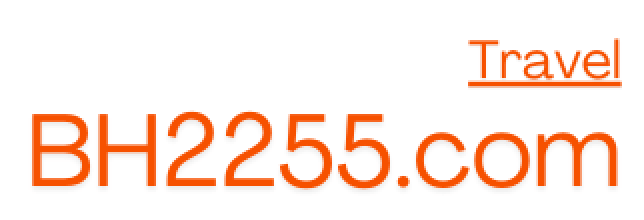从成都到若尔盖县城约有12小时的车程,空调大巴十分舒适,公路十分宽敞,却是少了几分我想象中初入藏区时该有的风尘仆仆。途经汶川时,见许多挂在山间的大牌子上写着“512地震遗址”,不免会想象大地震发生时的情景。公路再宽敞,毕竟还是紧贴着山壁,山壁陡峭,即使没有地震也常有落石,一场暴雨就能引发泥石流和塌方,更别提地震时山摇地动落石横飞的场面了。我想,如果此时发生地震,飞石砸向车子,那么车子不是被压扁,就是被撞入悬崖,我觉得撞入悬崖可能会比被压扁要好一些。我想,在自然界中发生再大的灾难,那都是自然本身,自然不会说一句抱歉,反而,该抱歉的最终还是我们。

12小时的车程于当时的我而言并不算漫长,大概是因为我越来越深入一个既向往又陌生的地方,我正向草原靠近,一群群牦牛在车窗外走过,牧民在马上指挥着牦牛的队伍,藏包被风吹得鼓鼓囊囊,经幡吹起了当地的信仰。

不过,这一路上藏民们的厕所都不太友好,我与同伴走到那些简陋的厕所门口时,发现这儿都是收费厕所,竟然要收1块钱。一阵阵尿骚味从里面飘出,我们不断后退,退到一堵墙边,浇灌起了野草,心中十分同情那些不得不进去的女人。
说到我的同伴,那还要回到成都说起,那天我吃完老麻抄手,回到青年旅舍,推开门,见房间多了三张新面孔,迫不及待与他们分享了“微麻”的经历,接着我们就聊到了一起。
这三个人中,有一个叫十七的摄影师,他是专门来成都给姑娘拍私房照的,就是那种穿得很少或者干脆不穿,躺在床上或者地上记录自己身体的照片,没一会儿他就出去见姑娘了。剩下的两个哥是结伴一起的,一个是农业专业的研究生魏然,不过他连青稞和小麦都分不清楚,给人感觉很水。另一个叫刘奥,他在南宁当警察,不过这个警察同志时不时就会讽刺我道:“你看看人家十七哥,拍的都是光溜溜的姑娘,你再看看你,拍的都是些啥。”有时候,我确实也是羞愧难当。
魏然曾在旅途中认识了一个同样姓魏的姑娘,魏姑娘一有长假就会去陪伴独自在若尔盖工作的妈妈,当年他们道别时,魏姑娘就邀请了魏然在暑假时到若尔盖找她玩,家里会好奶好肉招待。所以,在这个暑假,魏然叫上了他的好朋友刘奥,踏上了旅途。
得知我也要去若尔盖的时候,刘奥说:“咱们一起去呗!”
魏然瞪了刘奥一眼说:“人家姑娘就邀请了我一个人,你已经是个拖油瓶了,我得打个电话先问一下。”说着电话就打了过去,魏姑娘表示十分欢迎。挂了电话,魏然说:“那你就和我们一起去吧。”
比起不好意思拒绝,我更相信是因为魏姑娘的热情。
其实,我本来只是想到三个人一起去坐车会热闹些,毕竟有12个小时的车程,却没想到这两位哥一个电话就替我把在若尔盖的行程给安排了。
就这样,我们一起到了若尔盖。
我们在县城的车站等了一小会儿,魏姑娘就出现了,她把我们领到家中时已经傍晚。阿姨早已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一大盘牦牛肉让我欲罢不能,却碍于自己是第二个拖油瓶的身份,不好意思多吃,阿姨见我羞涩,在一旁干着急,她说使劲吃,要吃光。我使筷子的频率高了一些,不过最后也没有吃光,那盘牦牛肉实在也太大份了。
魏姑娘和阿姨都是都江堰人,姑娘平时在成都学习,阿姨则是因为工作被分配到了若尔盖。若尔盖海拔3400米,阿姨脸颊上散开的高原红如年轮般刻画着她在高原的岁月,她的皮肤显得干燥又粗糙,已经与当地藏民十分接近。丈夫和女儿常年不在身边,亲朋好友自然更少有造访,独居的生活,孤独是肯定有的,所以阿姨对远道而来的客人特别热情,使我深受感动。
吃过晚饭,我们被安顿在附近一家藏民开的宾馆。因为起初说是两个人,阿姨就只订了一个标间,见我们多了一个,便要多开一间,我们赶忙阻止,说一间标间足够。进了标间,两张不大的床,因为我是第三拖油瓶,就被分配一晚与魏然同床,两晚与第二拖油瓶刘奥共枕。
我躺在床上,回忆着那盘牦牛,不管怎么说,运气实在也太好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到阿姨家吃早饭,阿姨安排了车子和司机,早饭过后就踏上了游览若尔盖的旅程,第一站是九曲黄河第一湾。从县城到景区大约有六七十公里的路,公路铺得很漂亮,我们飞驰在层层山坡和广阔无垠的草原之间。我时常被一群群散放的牛羊吸引,虽然作为牲畜,它们与圈养的牛羊会走向同样的终点,但至少它们活着的时候算是潇洒。设想一下,如果把一头圈养了好几年的牲畜放到草原上来跑一跑,不知它会产生怎样的情感呢?

到景区后我们不得不加快步伐奔向观景台,因为天气阴沉,随时会下雨的样子。观景台在三千多米海拔的山坡之上,我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庆幸自己没有高原反应。
眼前就是黄河。
在我印象中,黄河是湍急而浑黄的,是汹涌的,是《黄河大合唱》中咆哮着愤怒着的,可眼前的河流却温柔平和,它弯曲成“S”形,像一条巨蛇游行在草原上,河水反射着天光,显得有些灰暗,但也绝不是那汹涌的席卷一路泥土的浑浊的黄色。我琢磨着它的名字——第一湾。

这是黄河年轻时的样子,如每个人的诞生,总算还是清澈,可它立刻就开始了漫长的旅行,每经过一个地方,都带走一些当地的石土,它的颜色发生了变化,它的性情变得凶猛,如同岁月的刻画,也是时间的沧桑,它一次又一次奔向终点,在渤海中释放出所有的性情。我望着这条河湾那望不见的尽头,脑中闪过一词,便是岁月长河。
雨最终也没有下下来,可能在别的地方已经下完了,总之没有下到我们头上,乌云被风吹走,迎来一片蓝天,黄河水也被映衬得很蓝,只可惜此时我们已经走下观景的坡道准备离开。作为被安排的观光游,与日落是无缘的,我们要赶往下一个地方。

车子在一块巨大的石碑前停下,司机大哥叫我们下车看看。石碑上写着“九大元帅走过的草原”,以及九大元帅的名字,有中文和藏文。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个草原就是红军走的那个草地。我开始想象当年的场景,想象这里没有修路时的样子,草会不会高过膝盖?我想象那长长的队伍,战士们会不会打草地里的野兔和土拨鼠来吃?他们会不会为眼前的美景感到惊叹?那可真是一次伟大的旅行。
接下来的一段路上常有羊群出没,羊群大摇大摆地在公路上踱步,每当司机大哥远远看到它们后就会放慢车速,他说:“这些动物。撞不得,撞不得的,赔不起的!”

来到一座破旧的寺庙前,便是今天最后的目的地了。这里名为巴西乡,寺庙原名班佑寺,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本来它会带着这个名字坍塌,不过到1935年的时候故事有所改写。当年过草地的红军有左右两路,右路军率先到达巴西这一带等候与左路军会合,可左路军那里出了些岔子,左路军的领率张国焘不但不愿意会和,还藏了些小九九企图破坏内部团结,针对此举,当年还是居无定所的我党中央就在我眼前的班佑寺内大雄宝殿进行了一次会议,会议进行得很有成效,往后,就少有人提起班佑寺这个名字了,大家都叫它“巴西会议遗址”。
巴西会议结束后,班佑寺遭遇了一场火灾被烧毁,在1937年重建。有趣的是,到了文革期间它又被人为摧毁了。我想到毛泽东带领的中央领导团在大雄宝殿内开会的场景,他们的革命最终成功了,可他们大概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这个寺庙会被情绪高涨的人民摧毁。

现在的班佑寺已被再次修复,但因为这里并不算主流景点,就少有维护,要不是见到几个当地人在这里转经,我甚至以为它已经被废弃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转经筒,黄铜色的转筒整齐排列在寺庙外围,显得神圣庄严,我兴冲冲地将它们转起来,自以为特别虔诚,魏姑娘却过来对我说:“你转反了。”
天空中常有黑压压的一群秃鹫盘旋,带着低沉的叫声,密密麻麻,我想到藏区有天葬的传统。

经过一间小木屋时,里面传出机械摩擦后的“咯吱”声,往里一看,是一个巨大的转经筒,转经筒下是一个佝偻的藏族老婆婆。老婆婆低着头像一头拉石磨的驴子般转着经筒,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她发现了我,停下来坐到转经筒前一侧的木质长板凳上,招招手叫我过去。
老婆婆用极其不流利的普通话告诉我:“转,转了这个好。”
我听从了老婆婆的建议,转起这个巨大的经筒,起步时稍有一些吃力,后来随着惯性几乎就用不着什么力气了。我转着经筒,一步一步,一圈一圈,经筒发出摩擦后的“咯吱”声。
转过几圈后,我在老婆婆对面坐下,老婆婆问我:“你认得毛主席么?”
我说:“全世界都认得毛主席。”
老婆婆点点头说:“喔……他来过这儿!”
老婆婆接着问:“你去过拉萨么?”
我摇摇头说:“没有,我还没去过。”
我问老婆婆:“您去过吗?”
老婆婆对我笑笑,她说了些什么,可我实在没能听明白,也只好以笑回应。小木屋里变得异常安静,经筒发出了由惯性转动停止前的最后一次“咯吱”声。我想这里太旧了,可能下一秒就会坍塌,可我知道,有经筒和虔诚将它顶着,无论如何也塌不下来。
“扎西德勒!”
回县城时太阳已经开始下落,此时车窗外的草原该是到了一天中最美的时候,可是一车的人都饿了,谁也没想要停下来看会儿风景的意思。我只好将头伸出车窗,后来我半个身子都在车窗外,风哗哗地吹在脸上,有点舒服又有点凉。

我的三个伙伴,魏姑娘,刘奥,魏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