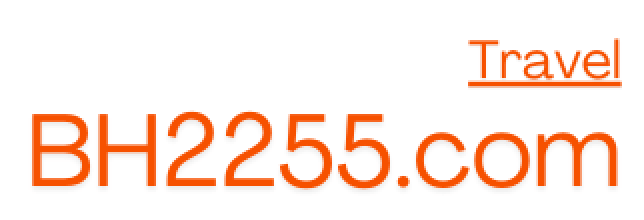“山峰无关公平与否,它们仅是危险。”
“我并非去往那里死去。我来到这里为了活着。”
——Reinhold Messner

四姑娘山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大峰、二峰、三峰、么妹峰从南到北排开,攀登难度也依次增加,么妹峰更是属于世界最高等级。
今年元旦,我则选择二峰开启登山之路。



徒步鞋只磨了半天,手套也是临走才寄到,虽然准备匆忙,但一背上70L包,顿时就有户外那feel了。可仅是走到地铁站,就让我知道自己离重装徒步还差个好腰,and买好装备的钱 (幸好这次有马帮)
(幸好这次有马帮)

巴朗山有夜间管制,所以我们住卧龙镇,在旅店旁的烧烤店跨年,次日早上再翻巴朗山到海子沟。队里好些老队员都互相熟悉,群里也是红包不断。我虽初来乍到,但在这个温暖大家庭里想慢点融入都难呀~

 上高原后会没胃口,今晚香香嘴儿走起,还有小姐姐带的冷吃兔
上高原后会没胃口,今晚香香嘴儿走起,还有小姐姐带的冷吃兔
2021年最后一份浪漫:在群山怀抱中,一群爱好相同的朋友吃着烧烤,聊着户外,惊喜地发现下起了雪,灯光温暖,街道宁静,卡车偶尔驶过留下微微痕迹,胖胖的老板围着围裙,我们守在烧烤架旁,捧一杯热水,让雪花轻轻飘落进去。



离开旅馆,垃圾联通就开启了我2天的断联生活。幸亏一起床就把新年祝福发了出去 。大巴停在邓生沟上防滑链,我们也趁机下去踩雪。拍日照金山和黄牛群、打雪仗、享受雪的纯洁和宁静。
。大巴停在邓生沟上防滑链,我们也趁机下去踩雪。拍日照金山和黄牛群、打雪仗、享受雪的纯洁和宁静。











四姑娘山景区有三条沟,双桥沟、长坪沟和海子沟,前两者是开发成熟的休闲游景区,户外爱好者则多在海子沟。去海子沟要签署各种文书,办理手续较久,加上上防滑链耽误了会儿,我们11点才入沟。



今日任务是徒步到二峰大本营,要赶在天黑降温前到达必须加快脚步。大神们冲前面,兰叔在中间拉,围爷在最后吆人。
以前能在长坪沟小跑,以为这次也没多大问题,但毕竟大半年没运动了,裤子又紧,给爬坡增加很多负担 。不过慢下来兰叔就会推你上坡,趴在围栏上会听见辛辛喊“雯青不要停”,真是又累又好玩。
。不过慢下来兰叔就会推你上坡,趴在围栏上会听见辛辛喊“雯青不要停”,真是又累又好玩。







海子沟风大,经常又是从背后吹来,稍微走慢些就容易吹感冒高反。幸好我在着装上做过功课,即便被吹瓜了,背上汗湿一大片,也没有着凉。
戴着墨镜、手套不好拍照,只是拿手机闪了几下。美景不需要构图,相机也拍不出双眼所见。





打尖包是去大本营路上唯一的补给点,据驴友说,之后的行进难度是前面的2倍,一般都是在这里吃午饭。我在高原没胃口,也感觉不到饿,只吃了两块奥利奥和一个草莓卷,吃啥都不如几口乐虎~


打尖包后,海拔继续升高。有一段陡坡很窄,马队经过时扬起漫天尘土,到底是大口呼吸防止缺氧,还是捏住鼻子减少TSP吸入嘞 。
。
当然也可以选择骑马,为第二天冲顶节省体力,但学生预算有限,要啥没有只有身板儿一个 。“好累哦 好累哦,我也想骑马
。“好累哦 好累哦,我也想骑马 。。。。。。”
。。。。。。”


 再累也不能影响拍照
再累也不能影响拍照







大本营前是个五六十度的大坡,海拔抬升100米左右。最后一冲,体累心也累,我只有爬二十步歇十来秒。这几天一刻不停地张大嘴呼吸。坡上人人都走走停停,石像一般伫立在风中大口喘气。所以,这是“绝望坡0号”吗-

17:00左右,终于爬到大本营。
大本营海拔4400米左右,我不知道是零下多少度,风力有几级,总之在煮饭的大帐篷里,运动后余温在几分钟内消失殆尽。我的手脚迅速失温,一跳脚趾仿佛就会断,即使运动产热也杯水车薪,手指更是麻木到不能弯曲,只能像筷子一样把小伙伴分的牛肉干勉强夹起来。
女生帐篷一搭好,我就立马冲进去。围爷和几个小姐姐小哥哥还有精力帮我们铺蛋巢,而我已经冻傻了,只有站在一边发抖,目光呆滞停止思考。以前川西游都是养老,如今才知道什么是户外,虽然被虐,但也很有意思 。
。


拿到行李后马上加衣服,可手僵到没力气拆包,只有用手腕像木棍一样把背包一点点撑开。坐下来没多久小腿也跟着僵了。
脱下外套裤子贴暖宝宝,动作一快就缺氧,一慢就失温。暖宝宝只在体温够的情况下才发热,我冰冻的脚相当于白贴。幽幽姐借给我羽绒袜套,兔兔也让我把腿放在羽绒睡袋里,但还是冻得麻麻的。不想看夕阳和雪山,也没动力走到男生帐篷去取暖,总之就是冷到呆若木鸡。

今天徒步14km—海拔3250m→4420m—用时5.5h,即使风大但温度不低。明天凌晨3:00冲顶,路程5km-海拔提升4420m→5276m,垭口处预计气温-20℃,6-7级风,山上才下过暴风雪,雪会厚,又再加上黑夜攀登,我担心体力不支,担心失温,更担心不能如愿登顶。
走到石头房子,围爷和辛辛在给大家煮晚饭。大锅扑腾扑腾,热气被头灯照成一束束的。婷婷姐在煮可乐姜茶,我回去抓起杯子就跑来守着,一杯下肚真暖和许多。


我站在帐篷最里面,不一会儿就缺氧了,嚼几口就面朝帐篷布狠吸几口气,好像确实能吸到一丢丢氧气,咱也不太清楚 。
。

我们七点半吃完饭就回帐篷睡觉了,毕竟明早3:00出发冲顶,夜间温度低,容易高反,不易入睡。
男生还要在星空下喝茶吃水果聊天,我一小白驴可不敢,贴好暖宝宝、戴上帽子,八点前就滋溜钻羽绒睡袋里了。


我果然睡的不踏实。通气孔留小了会缺氧头痛,留大点冷气刺激也不舒服。还好我的黑冰b1000比较给力,至少脚趾暖和了。糊里糊涂的到凌晨1:30左右,营地开始躁动,应该有队伍陆续起床了。


我大概2:20左右起床,一坐起来马上就有精神了。睡袋、衣裤、鞋子表面结了薄薄的冰,幸好睡前把抓绒、袜子、手机和充电宝塞到睡袋里,早上穿衣才不冷,手机也没冻坏。
穿着上,我的上装仍是速干+抓绒+冲锋,下装换上了滑雪裤,手臂和胸背再贴上暖宝宝,不影响活动,也不会出汗过多被风吹失温。
我穿好雪套和冰爪,往嘴里塞2块奥利奥,喝了一小碗热面汤就赶去集合。为减轻背包重量,我只背了20ml乐虎、一块士力架,还有钰婷姐姐给我的一块面包。我不习惯用登山杖,就索性没拿(下山时用登山杖还是对膝盖友好些)。
起始是一段约100米高的断崖,没有冰雪碎石,u形上升比较好爬。大家间隔一米,排队前行,虽然比较喘,但都能跟上节奏。

之后便进入雪线,大概四十度的坡。我外八字、全脚掌落地,就不易打滑。


再之后是挺长一段平地,雪大概没及小腿肚。有雪套和滑雪裤的双重保障,再踩着前人脚印走,不会打湿鞋袜。这一段很顺畅,虽然雪风大,但经历了昨天现在都还能接受,我也能掏出手机录像。



估计走了1km多吧,雪坡坡度开始变大,队伍逐渐拉散。在坡度转折点处,有人停下来补充能量,我也掏出冻硬的面包啃了一口。
此时无知的我忽略了向导的重要性,没有紧跟他们和队里大神的脚步。我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挑战从这里开始。


这段坡五十多度,有些许积雪,但很多碎石,不太好找稳定的落脚点,需要u形爬升。凭借我匮乏的经验也不太能看出u形路在哪儿,必须得紧跟前人步伐。
刚开始前面还有人,可以看见他们如何选择路。可我一弯下腰喘气,再抬头时已距他们快十米远了,头灯照及的半环区域内尽是碎石暗冰,很难分辨出路在何方。我环顾四周,身后也是一片黑暗,后来者的头灯有二三十米远。
黑暗放大了恐惧,站在这个陡坡上,身后仿佛万丈深渊。雪风不断动摇我的重心,我只有弯下腰来,头顶迎风,一边调整头灯、压住帽子,一边四处扫视找路。无边的黑暗包围着我,我不敢下撤,也不甘心,所以一鼓作气直线爬升去追前面的人。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到生命遭受威胁。
向上,但不知路在何方,一边找落脚点一边快速上爬,怕滑倒所以不敢减速,缺氧没有力气也不能停下;向上,会不会把我推向更危险的境地……我终于赶上了前人,跟着这个小哥和他的向导继续前进。
不知是累了、害怕了,还是风越来越大,只觉得坡度只增未减。我们三人就像黑夜里的孤岛,看着驴友零散的灯光在前面垂直通往天上,在身后垂直落入地心。
也不知到多少海拔了,每爬三四步就得停下喘气,一停就能感到雪风乱刮,如果挺直身板或者扭腰看身后,估计会被掀翻滚下山去。好在我逐渐适应环境,掌握节奏,也就没那么害怕了。
但既是向上,难度怎会不变?
走着走着,向导和小哥都在我身后,我成了那个探路人。坡度逐渐增加,巨石开始变多,冰面、雪和碎石混杂。落脚点藏在石缝间,前后相距甚远,得把腿抬高些才够得着。我快速计划路线,同时手脚并用向上攀爬。
或许是城市生活久了,“入门级”三个字让我轻敌。来之前只练过一次深蹲,偶尔打个空气拳,没练过攀岩,连上臂肌肉也只在手术拉钩时才训练到,所以这些状况我真的始料未及。
我还是相对顺利地爬上去了,感受不到累,感受不到缺氧,也感受不到冷,因为求生欲已经占据全身。
登山大佬Reinhold Messner说过:“我并非去往那里死去。我来到这里为了活着。”
上来以后有一段平路,能看见两三向导和驴友坐着休息,顿时轻松不少。但是,我又轻敌了。雪风越来越大,手脚在短短几秒内失温,我没法脱下背包拿水喝,只有加紧刚刚慢下的步伐。
刚刚一起攀登的小哥想要下撤,问我要不要一起回去。向导说垭口上面又冷又滑,我也担心后面更难,但总觉得刚刚爬的坡也很危险,石头那么锋利,还有结冰,摸黑下去我更害怕。所以直白地说,我最终登顶不是靠意志和决心,而是我胆小如鼠,想要活下去,憋到没法只有往上爬。
又是一个巨石陡坡。我没胆量单上,一边喘气一边等后面另一个小哥和他的向导。小哥在前,他掌控节奏,我在最后。身后已经一点灯光都没有了,只有前方三四点微弱的亮光像星星一般在天上时隐时现——啊—难道是垂直坡度吗,前方仿佛有几百米高/远,像在攀登通天阶梯。
现在是走一两步就得停下喘气,风力不减,温度下降,我累得弯下腰,又开始手脚并用。向导告诉我,绝望坡已经爬过了,现在是乱石坡,这一点欣喜好动人又好不真实。
“我好累,能不能停一下呀——”
“不能停太久,一停下大腿乳酸堆积不说,还会瞬间失温。
看,最顶上的那颗星星就是峰顶。”
此时才察觉,我手脚的麻木感已经到了新巅峰,踩在地上、抓住岩石,都感受不到力量大小。
我傻傻地对自己说:“要活着,要活着。”于是手重重地打在岩石上,让脚深深陷进雪里,不能轻易放松。
到垭口的最后一步,我已经没了力气,是向导把我拉上来的。垭口向上,就是登顶的最后176米(高度),需要手拉住铁链向上爬。驴友们会把登山杖插在垭口,在这里补充冲顶的能量。
垭口是一块三四平米的平地,右边是悬崖,靠两根铁链勾勒出安全与危险的界线,左边是刚登上来的乱石坡。
天还是黑的,垭口的温度说是有-20℃,风力6-7级,向导说不止,因为山上才下了暴风雪。
小哥把登山杖一插,嗖地躺下。我也一屁股坐下,费了好大劲才脱下背包。乐虎早就结冰,打开瓶盖,一小坨乐虎沙冰掉在雪地里,我捡起来吃了。手指又痛又僵,撕不开士力架,只有靠虎口握住,用牙齿撕,折腾半天弄了个口子,结果太硬只吃一口就丢回背包了。


5100米海拔向上,我每走一两步都得停下来休息。有些路段雪厚,铁链离雪面太近,得弯腰去抓,这种姿势让我更踩不稳,连续滑了好几跤,挂在铁链上。两旁即是悬崖,大风不断裹走我的温度。
积雪太厚踩不到岩石,冰爪太小需要每一步都很用力踢进雪里。我用手掌压住铁链,虎口代替手指握力,脚像榔头一样硬邦邦地向雪里砸。向身后望去,深蓝色天空和黑色大地间已可见橙光。我突然好累,哗地哭了出来,真的好累。

 。
。
 登顶小伙伴们的合照,大家都好厉害,而我已经冻到蹲不下去,只能弯着腰拍照
登顶小伙伴们的合照,大家都好厉害,而我已经冻到蹲不下去,只能弯着腰拍照来之前,我本想登顶后拍么妹峰、拍日出云海、拍周围群山,可一上峰顶就冻瓜了,想不起要拍照,真的好可惜,可人生不也像这样吗?
一路上最艰难的部分都没留下相片,翻看手机还以为自己在休闲游。

 离开峰顶十多米,才想起该拍照录视频了
离开峰顶十多米,才想起该拍照录视频了






 流了五个小时鼻涕,面罩已经冻硬了,还有头发上的结冰
流了五个小时鼻涕,面罩已经冻硬了,还有头发上的结冰
天彻底亮开,温度也上升许多。再看乱石坡、绝望坡和大大小小的石坡雪地,发现也没有黑夜爬升时那么可怕了,拍在手机里更看不出陡峭。
我想如果是天亮时爬,估计会轻松些?不过下山时还是得注意,毕竟坡度不会因为出太阳而改变。




 找找坡上正在下撤的驴友
找找坡上正在下撤的驴友我慢悠悠地向山下摇,一边拍照一边走神。可能是海拔变低了些,大脑可以运转,就突然想起我的微信签名:Danger is very real, but fear is a choice.








“户外”一词越来越被提起,容易给大众造成“只要能吃苦就能玩户外”的错误认识。首先“吃苦”的级别能达到何种程度?“吃苦”也不是简单硬抗,需要很多生存技巧,还有生理、心理的种种困难需要克服。
“户外”,从来不是那么简单。
大、二峰作为入门级雪山,这个“入门级”对于有登山经验的人来说非常正确(踩台阶爬黄山、长坪沟或是稻城亚丁根本算不上登山,我这次深有体会);对于我这种天真自信的小白来说,确又具有蒙蔽性。
好在我把雪山视作一生所往,虽然第一次爬入门级雪山都哭了,虽然我连自己到底入门没有也不清楚,但我总会回到那片土地去,去追寻宏伟的自然。
Reinhold Messner说:“山峰无关公平与否,它们仅是危险……我并非去往那里死去。我来到这里为了活着。”这确实道出了我攀登过程的感受。当你身处山川之中,你又会卑微地觉得自己的恐惧小题大做。
有人会被这句话劝退,也有人会因此入坑。我不希望不适合户外的人因为跟风而挑战危险的事,但希望我的描述也能唤醒那些属于户外的灵魂。

如果你能坚持看我啰嗦至此,如果我的流水账能让你有一点点心潮澎湃,说不定你也有一颗户外魂。那么,我想借用朋友圈一段话结尾:
“雪山攀登是一种什么感受,这如同人生一样,看似很短的距离,但真正开始走的时候才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越往上你越会累,你所走的每一步都会让你像走绝望坡一样,一直想着怎么还没到顶,但是当你一步一步坚持下来后,你为你的一切坚持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