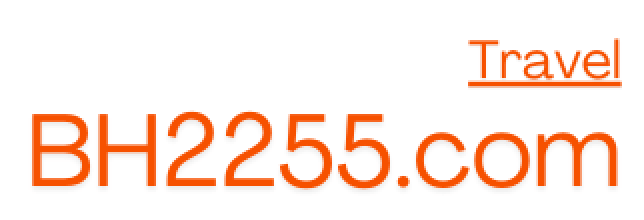杭州生活小记
迈向栅栏外的麦垛
1.

清晨,厨房的光线穿插着照亮卧室,屋内光线还是阴暗,晓涵的背影刚好挡住了半个阳光,裙子的侧面边角在闪亮着跳舞。晓涵冲好咖啡,一人一杯,她不爱加糖,一杯纯纯的黑咖啡,我喜欢放很多的奶粉和水蜜桃味道的果粉,带着淡淡水蜜桃的果香又充溢了牛奶味的醇厚,略微有些苦涩的咖啡可以冲淡吐司面包的酸气。完美的搭配,完美的早晨。
我初入社会不久,面对职场上的丛林法则极不适应,晓涵作为一个连简历都没写过,一直在学校里读书的女博士倒反复提醒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利用,想清楚这一点对很多事就会坦然很多。我极不服气,虽然我常常诧异,晓涵言谈举止与她所得出的结论极不相称。我们为此争论,论证的方式从生活琐事,到人际关系,再到家庭创伤,最后是名人名言。我们争论到结束永远都得不到结论。于我而言,像这样的一个裙摆飞扬的早晨,已是上帝无条件的馈赠,还有晓涵的咖啡。除了我需付的电费以外,的确是免费的。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证据,我不点破她。毕业一年,辗转四个城市,不是我刻意的计算或者有意为之,但每个地方差不多都生活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以色列、上海、邵阳、杭州。杭州已快到三月之痒,搬了两次家,换两份工作。我是在流浪还是在冒险,是在选择还是在逃避。当初毕业离开上海的时候仿佛是逃难一般,学校于我已失去了某种魅力,像戴上了一种枷锁,连同整座城市都判了我缓刑。我发现自己仍旧是十八岁时的自己。
2.

十八岁那年,离高考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天才刚蒙蒙亮,我从学校逃了出去,搭上了公交车,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上的是全封闭管理的私立学校,操场上围了一圈铁栅栏和监控器,每天排队吃饭,上晚自习,令人窒息。看了梵高那张《监狱》后,灰色的高墙下,犯人扭曲的脸围绕在一起,对我而言有着惊人的共鸣。我不爱说话,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书桌上堆满了复习资料,只有在课桌的角落里放了一本《追忆似水年华》。这是我的梦,普鲁斯特那个睡不着的夜晚从此开启了我的文学梦,也是我对大学最大的期待。可以想象,像我这样的女生会容易遭遇校园霸凌,什么原因永远说不清楚,正如路易斯说言,当初纳粹不知道什么原因恨犹太人,然后他们就去迫害他们,而当他们越迫害犹太人时,就越恨他们。你永远不要为恶开一个口子,只要开了就会排山倒海而来,人性如此。我也无须将自己摆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因为很显然,若是能调换位置,我也会立刻成为一个加害者,一个盯上了落单的小羊就不松口的群狼中的一只。我所在的班级,能考上大学的人可能都寥寥无几。我坐在最后一排,几乎与老师一样可以做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不要小瞧十七八岁的年纪,如同成人世界一般充斥着金钱,性爱,妒忌与谎言。只是年轻尚轻的时候还不懂如何包装自己。我实在无法沉下心的时候会走在教室的最后面站着,班级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你乏了就可以走到后面站着,只要不打扰其他人。每到这个时刻,我都觉得自己仿佛从生活的环境跳脱了出来,像上帝一般审视着这个地方,就像能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看到他们眼神流转出来的猜忌。
喧哗与骚动。我在墙上写下这五个大字。然后,像是一种天启。我看到这个世界上最甜美的微笑,像晓涵早晨的咖啡一样无私。有个坐在前排的女孩冲我回头笑了一下。如果可以定格下来,我就会去测量这个笑容的弧度,它在整个脸庞上的比例,它与整件教室形成的透视角度,与光线的折射,与我的视网膜的反映应当都是精密计算过的,它是闹市集中营里的被圣灵之光浇灌的一株白百合。请容我如此形容,而我相信我的天父不会因此责怪我。不知道如何形容,我又可以回到角落旁的那个阴暗的座位上坐下,充溢着所有被赏赐的幸福安宁。光并不在我这里,光在那个女孩的身上,积雪的洞穴里开始漫天下雨,顷刻间变成了海洋,而我可以在里面游泳。
卢梭说他想在第一次见到他“妈妈”的地方围上一层金栅栏,浪漫的法国人的确为他这么做了。而我能做什么呢?我无法拯救记忆,我不是画家,如果我拿着这幅画,说这是最伟大的人类作品,卢浮宫会不会驱逐我,我写的诗又总是缺点什么,叙述不够精确,想象力极为有限。我不相信艺术可以让任何东西不朽,我也无法保有一个人的心灵永远纯洁。感动会消失,女孩也已经褪色了。但若我至今仍在找寻,仍然在惊叹,让自己永远停留在十八岁,我是否就不算输了呢。我不是在逃避,我只是个行为艺术家。
3.

行李丢了装,装了又丢,每到一个新城市都要买把新菜刀。不停地搬家会让人不得不去选择哪些是最需要的东西。我列个清单方便那些同样打算长时间远行的人。
1. 一台十一寸的小电脑。携带方便,易于保存文件。
2. 阅读器。书到处携带是个累赘,丢了又觉得是件罪孽,送书给人就像送宠物一样,要选好人家,有的人拿去只是积灰,这也就算了,更有甚者,还会觉得你送的书碍眼。
3. 手机。虽然不满现代文明让人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方寸之间的小棺材,也丧失了刚上大学时不负责任的勇气,半个月的时间隐居山林,快开学时告知辅导员因为在山上信号不好所以没办法回复消息。如今没有谷歌地图或者高德地图,我可能寸步难行,最重要的是现在已经不敢半个月之后再回复任何人发的消息了。
4. 相机。我不喜欢拍照,人对待镜头是会矫饰的,但我决定开始远游的时候就买了这个小微单。拍下一座城市你最想纪念的东西,千万不要以为,你下次还能再回来,无论是人还是城市,每一次相遇都要当做离别。
5. 电饭锅。电饭锅真的可以当做随身携带着的万能小厨房,这可以保证无论生活在哪里,我也能不靠吃外卖和方便面活下去。
慢慢融入这座城市,气候和上海没有多大差别,我早已习惯江南水乡,只是还听不懂吴侬软语。雨天并不像上海一样总是绵绵不绝,又不一次下个痛快,像人想打喷嚏又打不出来。杭州的雨也会点点滴滴,柔情细雨,但有时候会突然倾盆而下,毫不吝啬,打你一个措手不及。白墙绿瓦,古城新街交错,最开心的事情是还能与曾经熟悉的老师和旧友相聚。
杭州的家可能是我在外漂泊的生活中最好的,以色列基部兹的宿舍里有蚂蚁窝,壁虎,上海租的单间有蟑螂、蜈蚣、蜘蛛,在老家的时候厨房偶尔会有老鼠,还有许多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昆虫。在杭州借住在一个姊妹家里。她比我大五岁,比起我的同龄人成熟不少,但比我大姐又多些童心。我早上贪睡,她很早就会起来祷告唱赞美诗,我半睡半醒时会以为声音是从窗外飘进来的,就好像中世纪的人被教堂的钟声敲醒。借住了两个月之后,因为换了工作,往返要三个多小时,不得已只能搬家了,后来这份工作也辞掉了,但是丝毫不后悔住在这里,虽然离市区较远,去哪里都要一个多小时的地跌,可房价物价都便宜。房间很简单,单身公寓,一个卧室、一个厨房、一个厕所,连着外面的公用阳台。
我还在上海的时候,晓涵就想来看看,她说她从来没有来过东部,我告之她如今我在杭州,若是你想来就和我挤在这个贫穷而闭塞的小屋里。她拿着行李箱就来了,每日早上给我煮咖啡,在阳台和她刚交往没多久就异地恋的男友打电话。有一次,早上醒来,她突然哭了,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她做了一个梦,发现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她男友的联系方式了,怎么也找不到了,就像他父亲当初从家里消失了一样。她问我,为什么人永远都走不出童年的阴影?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像我也没有走出我那个私立高中一样,晓涵不想回家。瘟疫的时候,她父母为了离婚的事情撕破脸皮,我突然想到在以色列的基部兹的时候,我和志愿者们一起看落日,大家谈起为什么来这个地方,每个人似乎都在逃避。或许是坚硬的现实,或许是难解的家庭矛盾。但我不是在逃避,要再重申一遍,我是一个战士,冲破栅栏迈向我的麦垛的战士。
4.

我的高中用栅栏将操场、食堂、宿舍还有教学楼都围在一起,我们每天都在栅栏里面生活,早上六点吃饭,晚上十点回宿舍休息,排好队去上课。我唯一能喘口气的时候就是上晚自习一个人去厕所里待一会。厕所是隔间有门的,有时能听到旁边的厕所有做爱的声音,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是谁。
栅栏外面有一片玉米地,学生们开玩笑,说那是一片天然的做爱圣地,免费的宾馆。老师们会严厉地告诉我们晚上不要离开学校跑到那里,晚上的玉米地窸窸窣窣,黑影耸动,好像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交易。我是不敢过去的,连看都不敢看,怕会被吸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但是到了白天,在栅栏的外面,玉米地的傍边有一大片空旷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小的高高的麦垛,我从来不是很清楚那是什么。从我这里看去,它很像一个岛屿,离开这个栅栏,越过玉米地,就可以站到那个麦垛上去了,我很想看看,从麦垛上往栅栏里面看是什么样子。每天早上,学校组织学生绕着操场一圈圈的跑,我就一遍一遍地路过我的麦垛,一遍一遍地想,从那里看这里是什么样子,我离开学校的时候一定要去那个麦垛里看一眼。
所以我的朝圣之旅,不是从上海出发的,我是从我高中的那个学校出发的,我一直没再回到我的高中,也没有再去过那个操场,也没站在那个麦垛上。如今我依然在栅栏里,眺望着我的麦垛,我还在前行,一点点往那里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