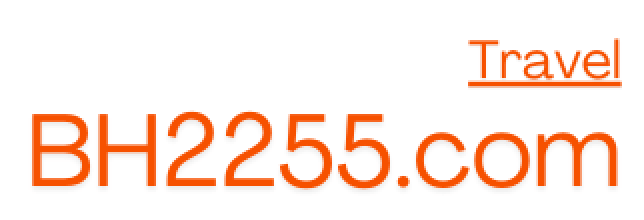距离跨年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来发生了大大小小让人沮丧的事情,折磨着每个人。
虽然在国外,但是还是无可避免地被疫情牵动着情绪。以至于我回忆起跨年这三天的行程的时候,像在脑子里搅拌着一桶粘稠的浆糊一样,混沌不明。时间久了,很多旅行时的感触也就再难拾取。只好写点连自己都看不下去的流水账保存下来。流于形式有时候也是一种必要的铺垫吧。


搭乘深夜航班凌晨五点钟从东京飞到上海,然后辗转到杭州和朋友见面,第二天又启程飞往成都,还没开始跨年就已经筋疲力尽。在我脑海里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几天灰蒙蒙的天气。不管是上海和杭州,还是成都,都是如此。好像在窘迫和无奈之中,为捱过即将到来的年关而紧锁的眉头。
我说,我们住的地方附近好像有一家口碑还不错的店,卖牛杂锅的,去吃吃看吧。于是又披上外套,因为怕吃得一身味道,所以里面只穿一条单衣,从酒店出来,打了个哆嗦,走进岁末的低气压的街道。
一家很小的店,没有复杂的装修,也没有海底捞式的关怀备至,服务员大妈在一旁心不在焉地玩手机,偶尔抬眼露出憨厚的笑容。入座以后,旁边是一桌大学生,应该是某个社团的年末聚餐,彼此称兄道弟,关系熟稔无间。这家店味道不错,对于旧居国外的我们来说,带着淡淡的药膳味的汤汁一滴入胃之后,两滴就能入魂。我们相顾无言,吃了两三大碗。之后决定去附近的太古里和春熙路走走。
有一句话说,成都是一座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因为生活安逸闲适,一出太阳,人们就什么事也不想做了,在街头巷尾摆龙门阵,打起麻将。想起早晨在飞机上看的一集纪录片,以不同的视角记录一座城市的72小时,午间茶馆里的唠嗑晒太阳的大爷大妈,和华灯初上时在火锅店门口排队吃饭的年轻人,构成了这繁忙城市里闲散的一景。
春熙路和太古里洋溢着快乐,踩着新潮球鞋的年轻人走来走去,带着甜度的气味像是在街道上撒了一把缤纷的彩虹糖。这种快乐也因为是跨年夜而显得更加的浓烈,让我暂时忘记了舟车劳顿的疲累。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个不太适合旅行的人,因为长久以来都保持规律的作息,而且对安稳的睡眠环境较为依赖,一旦作息被打破,身体上的状况便会接踵而至。这时突然刮起一阵风,我不禁又打了个哆嗦,说:“回酒店吧,有点冷。”
回酒店以后,用手机点外卖,想吃些新鲜的水果。等外卖的间隙,一边用酒店的投影仪看几家电视台的跨年演唱会,一边在浴室门口的小过道里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前台羞赧的小哥送来牛奶,我跟他道了晚安和新年快乐。关上门后小小的热闹在房间里像是满溢的啤酒泡沫一样四散开来,填充着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微博上看到武汉海鲜市场出现不明病毒的信息,一刷而过,没有在意。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觉得头晕,嗓子嘶哑难受,吃了粥店的外卖后,连忙吞下几粒随身携带的药片。无可奈何新年的第一天要在身体抱恙的状态下度过。午饭在楼下的餐厅里吃了一份微辣的干锅牛蛙,然后去了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回来之后又去了宽窄巷子和锦里。后面两个景点都已经充分商圈化,置身其中让人觉得茫然无措,转念一想觉得这种热闹在国外确实难得。


第三天坐高铁到了重庆,在高铁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醒来后觉得浑身乏力,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此身何处。在出租车上瞥见旁边的车子,车顶放着一块江小白的广告牌,才像是《盗梦空间》里看到那个旋转的陀螺一样,脑中仿佛响起炸裂的Trap,心情也慢慢激动了起来,勒是雾都!
我们的酒店在57楼,在49楼的时候换了一次电梯。房间里可以看到嘉陵江对岸那片密集的高楼,和楼宇之间隐隐约约的白色雾气。嘉陵江和长江不疾不徐地穿城而过,像是两个巨大的加湿器一样在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给这座城市加湿。
天黑以后,云蒸雾绕的水泥森林突然在暝薄的暮色中显现出原貌,霓虹灯和LED像是闪着幽光的藤蔓一样顺着地势和坡度占据每一座高楼大厦的外墙,整座城市像是旷野中聚集的磷火一样,诡谲而静默地燃烧着。赛博朋克之城。
街上挑着担子的小贩在卖一种染色的梅子,酒店前台让我们不要买,说香精加色素等于难吃。我跟微信上在重庆生活的朋友联系,他们也让我不要买,说那是“骗人果”。不过我觉得它红彤彤的荧光色还蛮符合这座城市的光怪陆离。这时候,突然走在我们前面的行人口袋里掉出两张小卡片,我上前一看,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觉得可爱,重庆真是个一到晚上就充满活力的地方。





离开成都和重庆,那之后又过了快一个月,暗淡无光的除夕夜过后,时间的齿轮正式地走到了2020年——一个承载了很多意义和希冀的年份。我在国外的生活也即将步入第三个年头。中途回国的次数屈指可数,之后不知会变多还会变少。
南唐的李后主写过:「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世上的事情过去的都过去了,就如同逝去的流水一样不复回返,一生沉浮,恍若梦境。频频醉饮,在醉梦中回到故园的小路。除此之外,又有哪里可以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