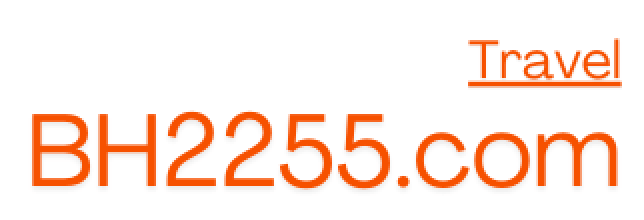我好比哀哀长空雁,
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
我好比鱼儿吞了钩线,
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
思来想去我的肝肠断,
今夜晚怎能够盼到明天。
小时候,经常从姥姥的收音机里听到咿咿呀呀的戏曲,什么过昭关、打龙袍、穆桂英挂帅。
虽然听不懂唱的是什么,但是那个场景和调调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
记忆里很久没有独自旅行了,久到连照片也开始模糊不清。
有一张图,很符合那时我的状态。

所以我骑着挎子,踏上归程。

过昭关
旅行的路上。除了风景。便是故事。
我没有故事,也没有酒。
却遇见过很多有故事的人。
也喝了很多下故事的酒。

走的太匆忙。
所以没有好好检查车的状况。
果然还没出兰州。车就熄火了。
按着油电油的套路,发现机油不够了。
加。
半桶机油下去,熟悉的马蹄声又回来了。

其实挺感谢我的挎子。虽然他小毛病很多。买不到配件。几乎没人会修。
但教会了我求人不如求己,没人会修就自己修。
偶尔的推车也弥补了我无法进行的体能训练。
而且,虽然骑不快,但他从未把我抛在路上。

在路上,留给大脑思考的时间很多。
在西北的山里穿行。
既见树。又见森林。
从2019到1997。

从前一天喝酒话别。

到第二天路过他的家乡。
再到昨日火车的擦肩而过。

也许人间,还值得。


出了甘肃到了宁夏又回甘肃。
好像总也不舍得和西北再见。
过固原,翻过有长征“胜利之山”之称的六盘山
作为一个湿人,我也即兴赋诗一首:
“你看这个路它又陡又弯,就像这个山它又绵又连”。

于是。终于到了陕西。
遇到了一个挎友。
准备说是一个大爷。但我叫他老哥。
我俩对向而行。我一路向东,他一路向西。
山水总相逢。在老哥把我拦下来的一瞬间。我突然想起出发前看的一个电影。
《过昭关》。
是一个77岁的老爷爷带着孙子骑着刚学会的摩托车去三门峡看文革时一起改造的老伙计的故事。
有时,我觉得我足够成熟,剩下的只是慢慢变老。
老人的话我们大多不爱听。觉得他们跟不上时代。很唠叨。
但现在我剩下的是慢慢成熟。

摩旅圈有句很俗的话:
四轮承载肉体。两轮承载灵魂。三轮承载着整个家。


老哥出来很久了。一天只跑300公里左右。
他说,年龄大了,不像年轻的时候了。
但是一天300公里和一天3000公里对有了目标的人。
又有什么关系呢。

老哥风餐露宿,吃住都在车场。
遇上了很多有趣的人。
跟我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就像电影里的李长福。
救下了生意失败想自杀的年轻人。
把钱给了在国道边索要安葬费的遇难的司机的家人。
遇到了为父母守坟的养蜂老人。
两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漫漫长夜相遇了。
酒逢知己。

其实我们又何曾不是这样。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孤独的旅程。
落在一个人一生的雪我们又怎能全部看到。
过罢昭关还有潼关。
过了潼关还有嘉峪关山海关。

老哥终于还是在新疆找到了20年前烈士的母亲并把照片交到了她的手上。
老人也在医院看到了多年不见的老友。


没有过多的寒暄。甚至只是几分钟的停留。
只有见面的一句朴实的“你吃了没”和离别的那句“赶紧走吧。路上慢点”。
不需要过多的言语。
所有的一切都在你我相见的那一刻已经明了。
电影里的老人很像《一个人的朝圣》里的哈罗德。
在得知老友病后,一个人踏上漫漫长路。
所有人觉得他们做的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
年纪大了。路途太遥远。坐火车客车飞机不就好了么。
但虽千万里,吾往矣。

电影的最后
老友还是去世了。弥留之际,他说,活着的时候能见到老朋友最后一面,他很满意。
他们都清楚这也许是这一生最后一次相见。
没有用力拥抱。不必用力告别。
所以。
走吧。走吧。
只是一定记得,路上慢点。


“路上慢点”。
“走吧,走吧”。
离家在外的游子也许对这句话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人生也许就是不断地告别。
不断地目送熟悉的背影一个个远去。
所以我从不愿告别。




离家的时候常听许巍、朴树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归家的路上,听得最多的却是《故乡的云》
“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夜幕已然再次降临。
我喝着烈酒。
感受着东南的和风细雨。
而此刻。
我离西北已有三千里的日月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