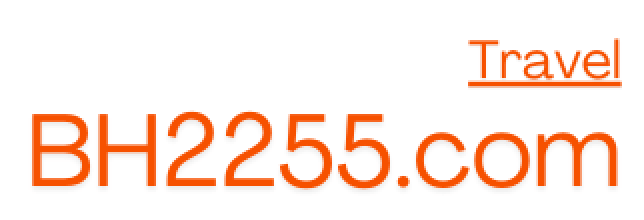摆渡车在一有岔路的地方停下。车上下来的游客被引导走左边,看我们大包小包的来住宿,告诉我们走右边。
走到寨子中心广场,迎接我们的不是民宿主人而是浓浓的牲畜的乡土气。
民宿是在携程上订的,早早的就告诉民宿老板我们过来的时间了,但民宿里没人。老板外出做工,老板娘外出采购。
按着老板在电话里的指引,我们在广场旁的几阶石梯下面找到了名为“古风寨驿馆”的民宿。老板要我们自己开门进去。这门也就是竹蓠芭的围栏。
又是一个夜不闭户的地方。



我们放了行李到广场周围转悠。


木板上刻的家规在墙上,石碑上刻的村规在地上。
村规很有意思。比如它规定:男子不留发髻,所持鸟枪不规定使用 ,生小孩或过世不种一棵树要承担违约责任。违约的处罚是“三个66”(66斤猪肉,66斤大米,66斤米酒)




一群盛装的小姑娘从离村委会不远的小学校里走出来。“你们是要去表演节目吗?”“不是,我们毕业典礼”她们欢快的告诉我们。姑娘们小学毕业了。



时近午餐点,我们转到一家饭店,店内一老爷爷气质不凡。他和孙女坐在一起的时候,是慈祥的神态。叉腰站立的时候又是轩昂的气派。他名滚拉往,78岁,50年代曾在北京当兵,后来回村当了村长书记。现在退位。如今大儿子是村长,开饭店的是二儿子。二儿子说他曾在张家界的饭店做事,疫情后饭店没生意,就回了村。

他跟我们讲他当兵的经历,讲芭沙的枪。他家墙上挂着6把长短不一的枪。



他在山坡边装弹放枪的样子顽童一般。




下午,为了看表演,我们回到上午下摆渡车的地方上了左边的游客通道。通道口有验票的寨门。表演3点开始。作为演员的村民陆陆续续过来候场。

寨门口是迎宾仪式,枪响客进门后,一个专职讲解员带着游客进寨到表演的广场,一路介绍芭沙的一些文化。
经过一片茂盛的树林。

滚拉往的生命树,就是这位老村长,人们称他为苗王。


表演在村里一块不大的平地上进行,有吹笙、舞枪、苗族舞蹈、婚嫁、镰刀剃头等等,持续约大半个小时。

不论是下场演的,还是场边候的,他们脸上欢快的笑容告诉你,这就是他们的自娱自乐。




女人们则更多的是关注她们自己手上绣的花。



镰刀剃头,估计全世界独此一家。每场表演都现场剃一个,一天有两场,整个部落男女老少总共2000来号人,人们不禁要问:这怎么周转过来的。


剃完了,顶部的发髻得留着。

摆渡车最后一趟是5点半。演出一结束,游客们匆匆去找摆渡车。寨子里又重归安静。

本打算跟着这回家的村民到别的寨中去看看,但顺着小路往山下走,一家又一家,层层递减,好像根本走不到头。

折返回来,从这两人的担子中买了人家刚摘来的小菜。再加上一只走地鸡,民宿老板娘为我们做的晚餐,家的味道。



凌晨,被鸡鸣叫醒。一阵安静后,山谷里又响起清脆的鸟鸣。推开窗户,一幅美丽的画卷展开:晨曦初露,晨雾缭绕在起伏的山峦之间,山峦松柏苍翠。
那首笛子独奏曲《苗岭的早晨》从记忆深处涌出。
我们庆幸自己在苗岭住了一晚,住在了推窗见景的古风寨驿站。







芭沙,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
枪,虽拿在手中,挂在腰上,但已失去了狩猎的作用。
芭沙,视树为神的部落。
树,生一棵,死也一棵。只要大树在,他们的生命就在。